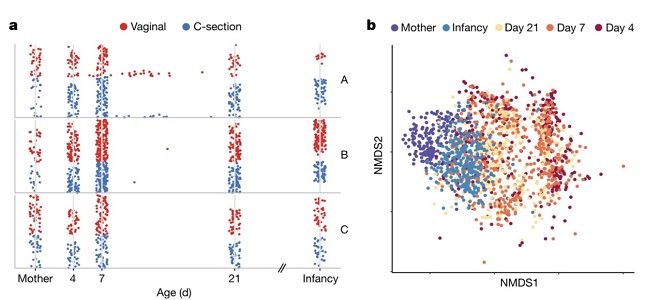中國歌劇表演藝術家田浩江的夢想,是讓更多中國歌劇走向世界。(記者曾慧燕/攝影)
田浩江在阿根廷科隆大劇院「浮士德」中,飾演魔鬼梅費斯特

田浩江在俄羅斯「白夜」藝術節演出歌劇「奧涅金」,在劇中飾演戈列明公爵。
(田浩江工作室提供/Joanna攝影)

田浩江飾演歌劇「圖蘭朵」的鐵木爾國王,圖為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出劇照。(田浩江工作室提供/Joanna攝影)

2014年3月,田浩江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的《奧涅金》飾演戈列明公爵,演出後與指揮家捷杰耶夫(左)及妻子廖英華(右)接受觀眾歡呼

田浩江演出「往事只能回味」,以費加羅詠嘆調開場
前言:從北京鍋爐廠的板金工,到被譽為「西方歌劇界最成功的中國歌劇表演藝術家」之一,田浩江走過一條充滿艱辛曲折的道路,但他一直奮鬥不懈,自強不息。而與眾不同的是,這位藝術家心中裝滿悲天憫人的情懷,他以生命來歌唱,用心靈來演戲。他呼籲所有學習西方聲樂的青年,要找到「藝術家的靈魂」。讓更多中國歌劇走向世界,一直是他的夢想。對深知「沒有藝術家永遠在台上」的田浩江來說,更是他夢寐以求的另類「舞台夢」。
田浩江在他位於曼哈坦林肯藝術中心附近寓所接受專訪時,暢談他在藝術上持之不懈的追求和未來的人生規畫,以下是訪談摘要:
問:你雖然在美國生活多年,並崛起紐約大都會舞台,名成利就,但發現你骨子裡仍非常中國,對故土魂牽夢縈。你近年馬不停蹄往來中美之間,未來有什麼打算?近年時興說美國夢、中國夢,你有什麼夢?
田浩江答:美國夢、中國夢,對我來講是一個「舞台夢」,舞台對我有著致命的誘惑力。我在美國已待了將近31年,對美國比中國更熟悉,因為這31年是中國變化最大的時期,所以當親友們叫我「回來」時,到底要回哪裡?中國人,根自然在中國,自然有「中國心」,我的「中國心」是在中國的舞台,所以我的中國夢是中國「舞台夢」。舞台也在變化,越變越大,越來越沒有國界,一個從事表演藝術的人,舞台是世界性的。
問:「紐約時報」譽你為「西方歌劇界最成功的中國歌劇表演藝術家」。你自1991年登上大都會歌劇院的舞台,並曾在世界上30多個著名歌劇院演唱,也是與世界著名歌唱家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和多明哥(Placido Domingo)合作最多的亞裔歌唱家。但你的簡介說你是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連續簽約19年的歌唱家?
答:首先千萬不要說我是「西方歌劇界最成功的中國歌劇表演藝術家」,實在不敢當,如果說「在西方歌劇界最成功的中國歌唱家之一」,加個「之一」,我會心安許多。我從1991年到2010年連續簽約大都會19年,最近三年沒有在那裡唱,明年回去演「圖蘭朵」,即將是第20年。
問:歌劇是一種高雅藝術,屬於西方文化,中國的歌唱演員想在這個領域取得成功非常難,所謂「高處不勝寒」,能攀登到頂峰的人很少,你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答:作為第一代在西方歌劇舞台上奮斗的中國歌唱家之一,那時在世界主要歌劇舞台上演出的中國歌唱家不過十人,30年後的今天,站在歐美主要舞台上飾演主要角色的中國歌唱家,依然不過十人。說明只有好的聲音條件是不夠的,你必須要比別人好,絕對不能自以為是,不要只跟自己的同胞比,不要只在別人的聲音上挑剔,要全面努力,你才有機會。我的「秘密」 之一,就是同一個角色,別人練三遍,我練十遍,因為在台上,你只有一個機會。
問:別人看到你的是輝煌一面,但相信你成功的背後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艱辛。聽說你長期生活在高度壓力下,多年來不吃安眠藥無法入睡?
答:是的,入行越久,愈發有如履薄冰的恐懼。歌劇的主要演員都沒有終身的演出合同,我在大都會歌劇院連續19年簽約,實際上是每個演出季都要重新續約,根據上個演出季的表現決定下一個合同。歌唱家的職業競爭殘酷,與每一個歌劇院的每一個合同都是競爭得來,沒有人會給一個沒有聲音、不會表演、缺乏音樂修養、不會做人的歌唱家合同,雖然你也許曾經有過演唱經歷。
在歌劇舞台上演唱是個夢,不是每個學歌劇的人都能夢想成真,但每個人都有追求夢的權利。歌唱家要有危機感,就像作家通常有痛苦感,登上這個舞台很難,下來卻很容易,一場演出沒唱好,可能就是在這個歌劇院的最後一場。
別人也許認為田浩江沒有理由恐懼,我已經站在歌劇舞台上30年,任何一個有30年歌劇生涯的演員都已經是奇蹟了,但我仍然有職業性的「危機」感,我無法為任何一場糟糕的演出原諒自己-不管是什麼原因。
問:你已經在舞台上久經考驗,但真想不到你每次出場前,仍會緊張,那你用什麼方法減壓?
答:確實如此,直到如今,我有時甚至覺得緊張得撐不住。我減壓放鬆的秘密武器,是唱小時候的歌「聽媽媽講過去的故事」、「讓我們蕩起雙槳」。每次臨出場,我都會在化妝間彈彈琴,唱幾句這些歌,兒歌能讓人回歸純真,保持童心。
問:金融危機後,西方歌劇界受到重創,資助古典音樂市場的人明顯少了,包括世界頂尖歌劇院亦不能倖免,最近也在削減歌劇製作經費和演員及劇院雇員的薪酬,對你們這些歌劇演唱家帶來什麼衝擊?
答:西方歌劇觀眾老化,加上歌劇院的不景氣,全美關閉的歌劇院中有五間是我唱過的。在美國和歐洲,約有數十家歌劇院倒閉或合併,可以維持的歌劇院大都減少了劇目和演出場次。通常,重要劇院的合唱隊和樂隊都有類似終身制的合同,而且演員工會往往會很強勢,但義大利歷史悠久的羅馬歌劇院,卻在最近解除了該院樂隊和合唱隊的合約,在歌劇界引起巨大震動。
不過,西方歌劇界的不景氣,並沒有減少歌劇的魅力,世界範圍內學習義大利美聲歌唱的人數反而倍增,在西方學習歌劇演唱的亞裔學生遍及義大利、德國和美國,僅紐約幾個音樂學院的亞裔聲樂學生,每年都在增加。
在中國大陸過去的十年中,至少蓋了50座國際水平的劇院,歌劇市場發展很快,譬如北京才運行了六年的國家大劇院,每年至少演出十幾部歌劇。在日本和韓國,歌劇演出是已是傳統,目前台北和台中都在建歌劇院,香港九龍的文化中心也將是亞洲的一個演出重地。
問:從西洋歌劇到中國歌劇,你跨越不同的文化和語言,融合傳統和現代,再在每個角色中找到自己。您一直鼓吹西方的古典音樂教育,呼籲所有學習西方聲樂的青年,要找到自己做為一位藝術家的靈魂,你的追求是什麼?
答:在美國生活了30年,離開中國越久,回歸文化母體的願望就愈強烈。能在國際舞台上演出中國人自己的歌劇,我由衷高興。讓更多中國歌劇走向世界,一直是我的夢想。沒有藝術家可以永遠在台上,多年來,我不安分的個性沒有變,寫書、演話劇、當導演及寫樂評、講課等,都是接下來我想做的事,我喜歡跟著自己的感覺走。
亞洲的觀眾很年輕,尤其在中國,中國原創歌劇的發展也令人矚目,你能想像在過去的30年,中國現代原創歌劇上演的劇目至少有200多部?我想,我個人的經驗,也許可以為中國歌劇事業的發展發揮作用,我們創辦的「我唱!國際藝術節」,培養中西方歌劇表演者是其中一步。
問:在這方面,未來有什麼具體計畫?
答:我會不斷地參與有關中國題材歌劇的演出和製作,目前我們有創作中國新劇目的計畫,另外我會盡可能地參與中國原創歌劇的演出。明年9月,我在北京參加首演的「駱駝祥子」將去義大利四個城市巡迴演出,以往很多年,我在義大利都是演出西方的歌劇,這次將在歌劇的故鄉演出中國歌劇,當然激動。另一方面,我會繼續幫助中國年輕的歌劇演員到海外學習,我太太創辦的美國亞裔表演藝術中心(APAC)一直在做這件事。
問:你曾經表示,當歌唱家容易,要當藝術家難,兩者有什麼區別?
答:當歌唱家容易的意思是,如果沒有內在的修養,歌唱就只剩下聲音,只剩下技術性的技巧,在舞台上如果光想著索取觀眾的掌聲,只追求報酬和榮譽,以自我為重,這不是藝術家。藝術家要把全副身心獻給藝術和觀眾,要永遠的探索聲樂作品的內涵,永遠的在圍繞歌唱的文化結構中磨練,這種磨練是痛苦的,沒完沒了,沒有止境。
真正的藝術家是真誠的、自然的、謙虛的,那是藝術的境界,我們本來就先天不足,歌劇不是我們生來就浸泡其中的文化,西方演員站在那裡就比我們像歌劇,所以我們比他們要多付出500%的努力,也許還不能成功。
問:您批評很多歌唱家「眼中無物」,在台上缺乏激情,表情冷淡,兩眼茫然,您是否認為很多青年聲樂學生缺乏聲樂表演、尤其是歌劇演唱的訓練,演唱時缺乏內心的激情和感受、注意力只在聲音?
答:歌劇要求演員要做一個全面的藝術家,能傳遞內心的情感,能打動觀眾,否則不可能立足舞台,更不要說西方的歌劇舞台。在中國演出時,我發現很多年輕的歌唱家眼睛裡沒有表情,沒有真實的激情,聲音都很好,很可惜。對想在西方歌劇舞台上發展的中國歌唱家,必須要能表演,要有西方化的、自然的表演,這就要有悟性,要先把自己的個性放下,因為你的個性裡可能還沒有那麼豐富的文化素養,尤其是西方的文化素養。
一個歌唱演員「眼中無物」是不行的,歌是要用眼睛唱的,而眼睛是心靈之窗。心靈的感覺來自一個人的經歷,來自文學、美術、生活中的歡樂和痛苦,愛戀和欲望,來自一個人對良心、親情,對祖國,對善與惡,對世間一切有趣事物的反應。
不過,很多歌唱家表情做作,沒有內涵,不感人,這也是世界性的問題,今天的世界極端商業化,物質化,自然影響表演藝術,追求信仰和精神的要求越來越淡漠,包括我自己都在掙扎。
問:對此你有什麼建議?
答:要多看書--這是我對所有學唱歌的人的忠告,看書教給你識別的才能。好的作品是有內涵的,每首歌都應賦與它生命,一句好的歌詞勝過千言萬語,一個眼神交流就能打動人心。我一向主張要用眼睛歌唱,能和觀眾用眼睛溝通和交流,才能和觀眾心靈相通,用藝術感染力讓台上台下融為一體,產生共鳴。
我認為,一個好的歌唱家,一定要讓觀眾通過你的眼神看到歌曲的畫面,歌唱家也是畫家,用歌聲描繪情和景。當你唱起「讓我們蕩起雙槳」,唱歌的人眼睛裡必須要有「海面倒映著美麗的白塔,四周環繞著綠樹紅牆」北海公園的美麗畫面;當你唱「松花江上」,就應有「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映入眼簾,觀眾就能跟著你走進這首歌。
因為你面對的是許許多多美麗的眼睛,從這些眼神中讀出許多東西。我也最喜歡音樂廳裡的「氣」,不論在那個音樂廳,氣始終存在。
問:你一向演的是歌劇,但台灣知名製作人王偉忠邀請你參與舞台劇「往事只能回味「(原名短波)的製作和演出,而且他也從幕後首次登台主演,你們兩個男人搭成一台戲,取得空前成功,在台北和上海都座無虛席,引發集體回憶熱潮。您是如何演繹這個角色的,為何你們有這樣的合作?
答:2010年我在台北首演原創歌劇「畫魂」,經朋友介紹認識了王偉忠,之前我曾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關於王偉忠製作的話劇「寶島一村」的文章,覺得這個人不一般。在台北見面兩人一聊,發現在70年代的少年時代,都偷聽對方的短波播音;王偉忠的父親是軍人,我的父親也是,當然他們也是敵人。當年是歷史使他們分隔在海峽兩岸,今日卻也是歷史使我和偉忠走到一起,這是很有意思的生命機緣。更不可置信的是,我倆都有一個哥哥,都因癌症去世,與哥哥們都有一段愛與衝突的糾葛。這種兩岸共同又不同的特殊成長經歷,讓觀眾感到熟悉又新鮮。
問:從「我歌我哥」到「往事只能回味」,您用自己低沉渾厚的嗓音不再歌唱別人的故事,而是輕聲訴說自己的故事。表演藝術家是您最自豪的身分,這個身分使得您有「塑造人物」的本能?
答:在舞台上,我要變成另外一個人,這是我的專業。我要通過表演演繹別人的精彩,別人的生活。然而,在一定層面上,表演是技巧。在反覆詮釋別人的故事時,自己也在沉澱自己的過往經歷。任何一個搞創作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在自己的人生經歷中尋找藝術感覺。於是「我歌我哥」誕生了。人對了,契機就到了。
我用自己最熟悉最擅長的方式,為大家講述了與哥哥的故事。但我不是專業的話劇演員。我也因此完全沒包袱,因為我就是演自己,我的情感從內心深處生發出來。那不是做出來、演出來的,是真的。表演最大的難處是「真」。因為大多數演員都不願、也不敢暴露自己。我和偉忠兩人做到了,都敢於在觀眾面前毫無保留暴露自己。
問:你今明年的行程都排得滿滿的,最近的安排是什麼?
答:「往事只能回味」應2014北京首屆「國際奧林匹克戲劇節」邀請,將於今年11月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公演。我還打算將「往事」一直演下去,且計畫帶到舊金山、紐約等四個城市巡演。中美間來往多年,中國在經濟、軍事等領域高速發展的同時,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要想與國際接軌,就需要有藝術水準、有國際水平的精品文化產品做保證。「往事」是如此真實、樸實,這種情感的表達是當下人們最需要的,它就是這樣的文化產品。
問:你說「沒有藝術家可以永遠在台上」,但又說你的夢是「舞台夢」,兩者之間如何平衡?
答:我本來考慮逐漸的走下歌劇舞台,在「知天命」階段,做一些另類的事情,但「天命」似乎暫時不讓我離開歌劇,明年我至少有六部歌劇在日程上,除了隨「駱駝祥子」去義大利巡迴演出, 還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再次跟大師多明哥合作,演出威爾第的歌劇「西蒙博卡涅格拉」。
我還會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再次演出歌劇「圖蘭朵」,這將是我在那裡演出的第20年,會很難忘。如果「往事只能回味」能如願來美國巡演,在蘇州夏天舉行的ISING(國際青年歌唱家藝術節)能籌到資金繼續進行,明年可能是我演出生涯中最繁忙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