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一现象,索维尔批判的角度,是知识分子的智识,而非知识分子的道德——索维尔这种奥地利学派思想家,并不那么确信谁的道德一定就那么高或那么低,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维尔所要批判的,恰恰就是道德感爆棚,而智识却未必过关的知识分子。
他认为知识分子因为拥有智力上的优势,特别容易把自己当成上帝——以为自己可以突破能力与理性的限制,却忘了自己作为人的有限身份,从来不必为自己的理论、言论负责,因此很容易危害社会。
书中列举了著名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时大量胡说八道的惊人案例。
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罗素面对正在重新武装的纳粹德国,却主张为了和平,英国应当“单方面裁军”,在英国社会产生了强大的绥靖思潮。
又比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在30年代拼命为纳粹辩护,为种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撑,但是理念产生的后果——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不用他来负责,直到二战结束,海德格尔继续在大学讲课出书,然后享誉全球。
当然,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只是其中一个,比他名气更大,影响更坏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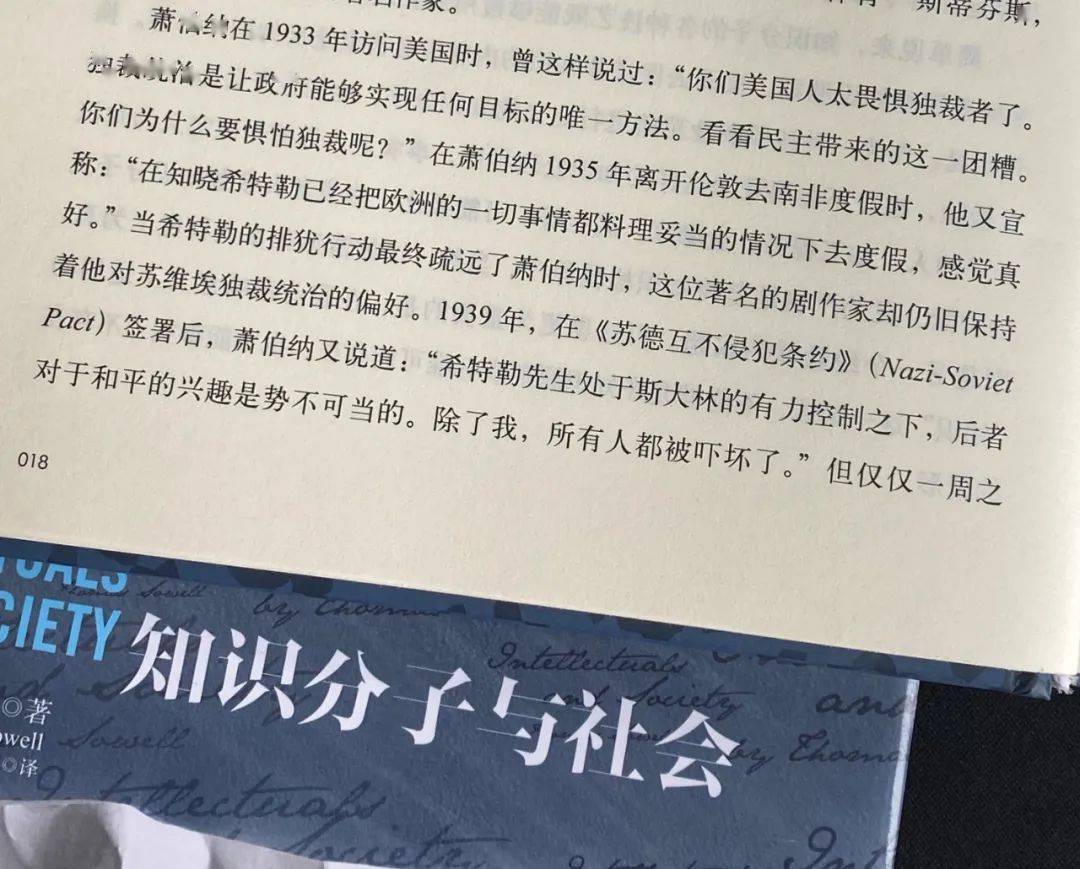
▍识别坏思想的三大铁律
那么,如何识别出坏思想、坏知识分子?索维尔提供了3条铁律。
◎ “圣化构想”
所谓“圣化构想”指的是,那些枉顾人性的复杂,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在头脑中构建一个完美的改造社会蓝图,认为一旦实现了,就会建成人间天堂。
在索维尔看来,任何社会都混杂着善与恶,人类历史上从未缔造过完美的社会,未来也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好的知识分子,不会承诺最好的东西,而是小心的去选择最不坏的那个。就像丘吉尔所言“与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只不过是最不坏的。”
有句话,可以说是为“圣化构想”者量身定做的:那些把人类引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的意愿铺设而成的。

◎ “辞令技巧”
所谓“辞令技巧”,是指自己的思想、理念在现实中明显失败后,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错误,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合理化的借口。
由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喜欢美化自己的理想愿景,以至于一直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再加上写作和诡辩本来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因此,面对错误,非常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材料或者词汇来替自己狡辩。
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不仅提供了识别坏思想、坏知识分子的简单方法,还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到自己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 “不是媚权,就是媚俗”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长久以来没有定论,但在索维尔看来,知识分子就是理念的动物,他的思考路径一定是以理念为起点,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为终点。
然而,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把这个逻辑倒过来——从现实世界出发,用理念要么迎合民众,或者谄媚权贵,那就是对理念的亵渎和玩弄,这是“坏知识分子”的标配。 例如,许多大学教授,为了迎合民众,今天建议政府向富人征收重税,明天建议广发福利,后天开始煽动对他国的仇恨......
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说:“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仅体现在反抗权力的蛮横上,也同时体现在抵制群氓的愚蠢上。”
可见,坏思想不只是谄媚权力,还喜欢迎合大众,在互联网时代,后者更为普遍。
▍ 《知识分子与社会》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解剖,更是提醒无数普通人认清人性原恶的镜子
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并非剑指所有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书中他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仅仅从理论入手,且最终只生产理论的人。因此,自然科学家、金融家、工程师等都不在他“知识分子”概念之内。
反之,而从没做过生意也没开过公司的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却因为自己的终端产品是理论,而被认为是知识分子。
他剖析的对象是公共知识分子。在索维尔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必对自己理论的后果负责,才会奋其私智,花样翻新的制造新概念,企图以自己的观念更新世界、改变历史。
此外,这本书既是对知识分子的解剖与鞭挞,也是提醒无数普通人认清人性原恶的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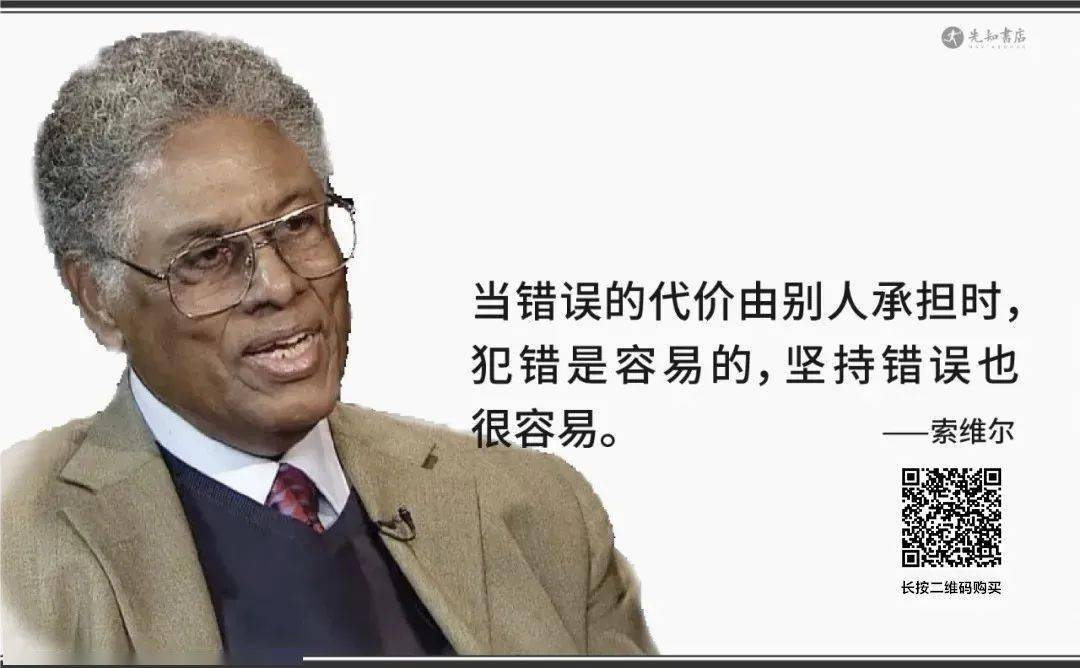
在书中,你会看到哪怕有那么多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哪怕有那么多杰出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如米塞斯、哈耶克、丘吉尔等都预言乌托邦必然失败,那些以良心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依然视若无睹。
你依然可以惊愕地看到罗曼·罗兰把记录事实真相的《莫斯科日记》束之高阁,说50年后再出版;你也依然可以看到萨特为了捍卫苏联而攻击昔日不够坚定的战友。
这些所谓的时代“良心”们,很难说他们存心撒谎,正如哈耶克和索维尔指出的,为乌托邦鼓与呼的人们,并不是他们有什么道德上的恶意,甚至他们比一般人还可能更具有同情心。
作为一名90高龄的美国著名黑人思想家,索维尔反思知识分子与社会,批判激进主义,会比常人遭受多10倍的压力,在巨大压力下,索维尔凭他睿智的思考、完备的知识结构、知识分子的道德坚守和一份“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让该书一经问世,即折服整个知识精英群体。
有人说:“读完这本书,掩卷而思,眼前仿佛站着一位解剖大师,他把知识分子一个个拉上解剖台然后写了一本详细的分析报告。”
而这份解剖报告就是——《知识分子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