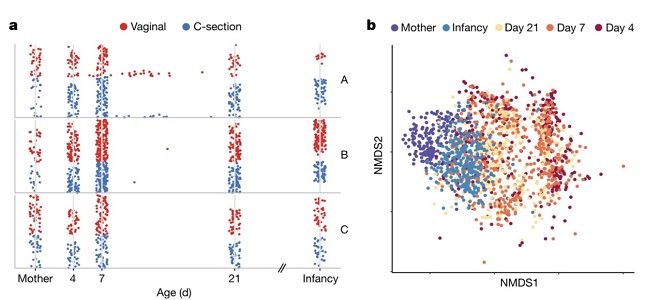首先,研究人员将袋子纵向切开,小心避免碰乱里面大量撕碎的纸片。然后他们对袋子里的物品进行大致的检查,取出食物残渣、垃圾,或者在急于销毁证据的混乱中混入的任何其他东西。
他们正在努力恢复大约4000万到5500万张纸,这些纸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最后几天被东德秘密警察撕碎并塞进袋子。
当民主抗议者在1989年和1990年冲进秘密警察分局时,他们发现警察正在里面工作,碎纸、化浆及手动撕毁文件。被称为斯塔西的国家安全部正在拼命销毁过去40年里它对本国公民进行间谍活动时收集到的监视记录。
大部分材料——被烧毁或碎成小块——已无法挽救。但有些袋子里的记录只被草草撕破,打算以后销毁。东德的活动人士设法阻止了对它们的销毁。
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做法,但有些人觉得有点疯狂,有点完美主义”。已有大约500个袋子的文件被恢复,还有15500个待处理。


斯塔西档案的通讯和研究负责人达格玛·霍维斯塔特(Dagmar Hovestädt)说,档案馆的中心原则是“帮助人们了解斯塔西如何干涉他们的生活”。自1992年以来,研究人员一直为前东德公民提供查看他们的个人斯塔西档案的机会,这将是一件五味杂陈的人生大事,因为他们的斯塔西档案通常会揭露出家人、朋友或邻居向斯塔西报告了他们的活动。现在,曾被斯塔西监视的许多受害者已接近生命的尽头,拼图者争分夺秒地工作,让他们能够选择在死前查看任何被恢复的文件。
西亚德·阿卡姆(Siad Akkam)是一名学生,有时会来民众申请看文件的办公桌坐班。阿卡姆说他们通常带着明显的矛盾心理:“你能看到他们带着一点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我应该这样做吗?我应该知道吗?”很多拿起申请表的人都是受害者的孩子或孙辈,希望能够说服亲人查明真相。
大约八人组成的轮换小组在这座大楼里工作,这里曾是斯塔西的总部,以及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埃里克·米尔克(Erich Mielke)的办公室。其他人则在斯塔西以前的地区中心工作。霍维斯塔特说,“在一个40年来组织镇压的历史遗址当中”推翻斯塔西的工作,这是一种特殊的正义,“这是这次行动的核心。”在这栋明显是东德风格的建筑里,到处都是灰色和棕色,她说,“你会想起自己身在什么地方。”


一个袋子里可能不仅有纸,还有邮票收藏、一个东德共产党大会的电话簿,或者斯塔西的培训材料,里面包含了马列主义文学和如何窃听电话或清洗枪支的说明等等。
在开始处理任何袋子之前,工作人员要先确定大致的主题。他们寻找以“IM”字母开头的名字,代表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即“非官方合作者”——这些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任何与斯塔西监视本国公民有关的事都会被优先处理。主要装有培训材料或官僚文件的袋子将被认为不太紧急后送回仓库。

档案员露丝·齐默尔曼在一份拼合文件的背面小心翼翼地贴上胶带。
这些袋子有自己的层次,就像地质底层一样,研究人员尽力保存它们。当内容被确定是重要的(无论是对历史学家还是对受害者个人),研究人员会分阶段移除纸张碎片,寻找匹配的边缘、笔迹或纸张。
如果碎片太碎,研究人员有时会用一种名为ePuzzler的机器重新构建它们。但是文件碎片实在太多了,ePuzzler也无法显著加快项目的速度。


这些团队将可以手工重建的碎片放在一张桌子上,用档案胶带将每份文件拼接在一起。从这里,完整的文件被放入斯塔西档案。他们没有对外宣传,也没有通知档案中提到的任何人——该小组的理念是,应该由受害者来选择是否查询自己的档案。
关于斯塔西线人和官员的信息则是另一回事:它不被视为隐私,因此记者和研究人员可以申请查阅。在1990年代,由于一个线人的信息被披露,许多人的职业生涯和婚姻都被毁了,经常根据这些档案揭露名人的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甚至给它们起了“恐怖档案”的绰号。
近年来,披露的热潮有所放缓,但其后果仍可能改变人生。“在某些情况下,你必须改写自己的生活,”霍维斯塔特说。
佩特拉·黎曼(Petra Riemann)第一次听到她父亲的双重生活是通过一则报纸的报道。卢茨·黎曼(Lutz Riemann)是一名东德演员,因在电视上扮演警察而出名。但是,根据《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2013年看到的文件,他也曾是一名线人,监视着家人和朋友的动向。黎曼在接受采访时说,她知道他有时与斯塔西的外国情报部门合作,但她把他想象成某种詹姆斯·邦德式的人物,而不是利用私人晚宴和生日派对收集亲近朋友情报的那种人。
“他利用我们的家庭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她说。

斯塔西记录档案馆就在曾是柏林斯塔西总部所在地的同一栋大楼里。
不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当她后来发现他有秘密的第二个家庭时,她不知道这只是一次简单的婚外情,还是像他所说的,是他斯塔西工作的一部分。她说她和父母已经不再说话了。
黎曼写了一本书,讲述她和记者丈夫托斯滕·萨斯(Torsten Sasse)的经历。她说,从这些文件中获得的知识,值得付出痛苦。“你可能会在这些文件中看到一些永远困扰你的东西,”她说,“但问题当然是:你能生活在谎言中吗?”
本文无法联系到卢茨·黎曼置评。不过他曾在2013年接受《周日世界报》采访时承认自己做过线人,并表示他——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那么做的。
到目前为止,重建的文件中包括了一些有关异见人士的信息,比如已故作家、政治人士尤尔根·福克斯(Jürgen Fuchs),他曾被斯塔西关进监狱,而后被驱逐到了西德。还有一些文件揭示了东德运动员的禁药使用情况以及西德极左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的活动。


参与恢复工作的档案员露丝·齐默尔曼(Ruth Zimmermann)说,这个项目是在实践德国人的“Aufarbeitung”理念,意思是去处理往日的不公。
不过,在斯塔西档案中有一个巨大的空白:只有本土监视的记录,没有海外监视。斯塔西外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大部分已被销毁,也就是说在西德工作的线人不用面临同样的曝露。在加顿·阿什看来,这种不对等会导致一种印象,就是这个项目代表着一种“胜利者的正义”,即西德对东德的胜利。
“这加深了东德作为受害者的印象,”他说,“因为被揭露的官员和线人都是东德人,当然在西德有不少特工,他们可能至今还过着受人尊敬的退休生活。”
作为一名1980年代在东德工作的英国记者,加顿·阿什曾被斯塔西怀疑是外国情报人员。按照他在自己的《文件》(The File)一书中所说,斯塔西从一系列人士那里收集了有关他的情报。

档案员安德里亚斯·罗德尔
其中一名线人是位东德老太太,两人在一次展览上偶遇,后来成为朋友。只要同意监视他,她就可以有机会去西德看望逃到那里的儿子。“她比我更像一个受害者,”他说。
“我们这些在华盛顿或伦敦长大的,至少应该问问自己,如果生活在独裁统治下,我们会怎么做?”加顿·阿什说。“我会想我应该是个大无畏的异见人士,但也许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当我们要对一些人妄下定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这一层,比如这位可爱的老太太,她作线人是出于一个非常合乎人情的原因:她希望跟儿子重聚。”
以现在大约每年20个袋子的速度,这个项目需要耗时几百年。而其中许多文件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看到。研究人员说,甚至有些人在填了申请表后再也没来查阅他们的文件。
然而这符合该项目的原则:没错,你有权去查明并质问那些背叛你的人,霍维斯塔特说。然而,“你也理应有权不去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