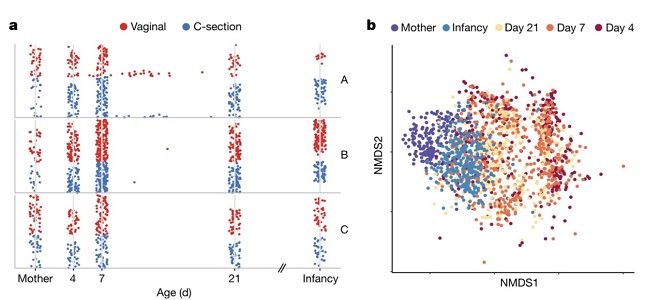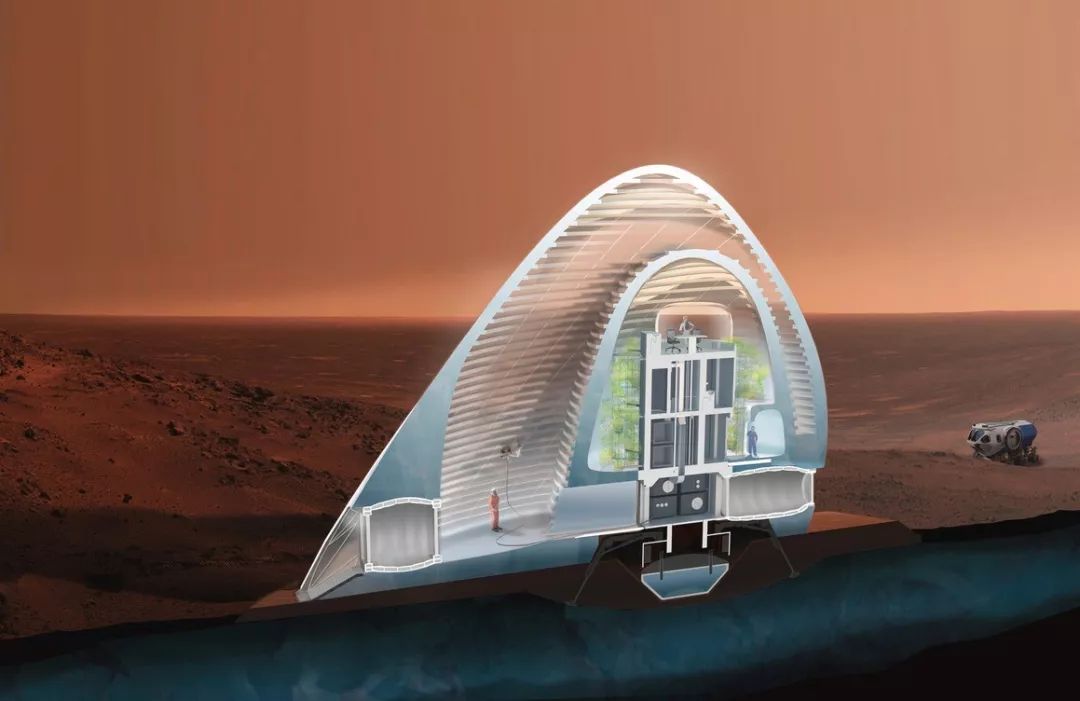她走进咖啡馆,脸上的口罩写着“我不害怕,你也别怕”。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跟着她进来,看她在我身边坐下,然后就不见了。另一个穿背心、戴灰色帽子的男人在外面等着。
我们走出去时,他跟在了后面。
那时我在采访维奥莱塔·格鲁蒂娜(Violetta Grudina),俄罗斯北极城市摩尔曼斯克的一位活动人士,与正在狱中的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A·纳瓦尔尼(Aleksei A. Navalny)是盟友。她刚刚结束一场绝食抗议,当时正在恢复中。在不间断的监视下,她承认自己处于一种隐约的、令人麻木的绝望中。
“我们都被困在一个陷阱里——暴君设下的陷阱,”格鲁蒂娜说。“这种麻木是源自你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但什么也没有改变——这让人很难过。”
俄罗斯是一个要么没有任何改变,要么一切都改变的国家。在本周末的全国议会选举前夕,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总统那包裹着一层舒适的稳定性的威权统治达到了一个新顶点。在许多人看来,普京依然是一位英雄,尤其是因为他在外交上的坚决自信,而反对他的人已经败退到自欺欺人的绿洲或平行世界里。
从8月24日到9月7日,我和摄影师谢尔盖·波诺马雷夫(Sergey Ponomarev)从北向南穿越俄罗斯——从北极到高加索的车臣共和国,行程约4800公里——以求探明为什么在位20年的普京仍能掌控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五天的火车卧铺旅程,带我们走上了一段俄罗斯特有的、纵贯其辽阔疆域的竞选路线。在摩尔曼斯克,为了让格鲁蒂娜无法参选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强行让她住进新冠病房。在车臣,对该地区强人统治者发起挑战的人,似乎追求的是尽可能少得票。
“你不能说,‘换个人来接手吧,’”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候选人阿特约姆·吉尔亚诺夫(Artyom Kiryanov)在俄罗斯中部的瓦尔代湖畔对我说。“根本没有这样的替代选项。”

摩尔曼斯克地区的一个乡村市场里,一个人在自己的汽车上贴了朋友的竞选海报。许多反对派候选人被取消了资格。

活动人士维奥莱塔·格鲁蒂娜受到了不间断的监视,她与狱中的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A·纳瓦尔尼是盟友。

8月下旬,北极海岸泰瑞伯卡村的一些俄罗斯游客甚至不知道即将举行议会选举。
统一俄罗斯党本周看起来是志在必得,不过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抗议投票,尽管选举从根本上是一种安排好的活动。我们感到人们的情绪主要是恐惧——害怕因为异议受到惩罚,或失去他们已有的东西,或贫穷与战争的阴影。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人对官员腐败、工资增长停滞、养老金过低和价格上涨已经忍无可忍,但是愿意去面对后普京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人却少之又少。
“我担心一旦出现变局,”生活在南方城市沃罗涅日的工程师维塔利·托卡连科(Vitaly Tokarenko)说,“就会有流血。”
此行让我们亲身体会到俄罗斯的政府监控在不断扩大。在摩尔曼斯克,穿背心、戴灰帽的男人跟着我们穿街过巷,来到我们的酒店门口。一个半小时后,拍完照片的格鲁蒂娜离开了,他没有跟着。
“他可能在等你,”她发短信告诉我。
索洛韦茨基:创造“绿洲”
向南行驶的夜行火车和渡轮带我们穿过北极圈,来到位于白海的索洛韦茨基群岛。坐落在冰川形成的壮阔丘陵间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最受尊崇、翻修费用最高的修道院之一,该教会是普京的核心支柱。
因此,能见到奥列格·科多拉(Oleg Kodola)非常难得,这位52岁的旅游经纪就在修道院外工作,他坚持认为,“任何支持本届政府的行为都是极其恶劣的。”他说他投给共产党,这是削弱统一俄罗斯党的最大希望。
与其等着政府修好他餐馆前的马路,从他使用的码头移走船只残骸,他打算自己动手。这是反映俄罗斯一个全国现象的生动案例——异见者正退回到自己的世界。
“我们计划在这里创造一片绿洲,”他说,“表明在没有国家的地方,一切都很好。”

索洛维茨基群岛险恶的一面显示了政治镇压可能导致的后果。

最近对这些岛屿的重建主要关注精神世界。

而早期苏联人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监狱营地,成为了后来古拉格的前身。

在一次朝圣者之旅中,导游很少提到那段历史。
在曾经是劳改营最臭名昭著的监狱的一座山顶教堂,导游奥尔加·鲁西娜(Olga Rusina)对狱警在教堂大门上凿出的诡异窥视孔,以及草地上据说是行刑队用来瞄准的一圈石头只字不提。
“我不想让这些悲剧给你们带来太多心理负担,”她对一行人说道。
她的态度让我很吃惊,因为她曾说过,她的曾祖父、曾祖母和另一个亲戚都在索洛维茨基劳改营里丧生。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家庭的悲剧归咎于个人,而不是国家。把他们送到这里的不是克林姆林宫,而是对他们心怀嫉妒、指责他们是富农的村民。其中暗含的一层意思:民主是致命的。
瓦尔代:特权阶层的权力
再往南,树木越来越高,人口也更加稠密。但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中间,在原始的瓦尔代湖郁郁葱葱的绿色岸边,仍有可能遇到彻底的寂静。
这种寂静偶尔会被轰鸣作响的直升机打破。普京喜欢来这里,越来越多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也是如此。塔蒂亚娜·马卡罗娃(Tatyana Makarova)之所以能看出来这一点,是因为她所在的亚舍罗沃村及其周边地区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几乎切断了村民前往湖泊的路。这些建筑群门口有老鹰和咆哮的熊的雕塑,里面有自己的教堂,气势十足的围墙上装有铁丝网。
现年48岁、经营着一家小型清洁公司的马卡罗娃带头反对新的建筑工程,与她的邻居们一起跟俄罗斯一些最有权势的男人进行了斗争。她的故事表明,俄罗斯人并不是在试图推翻普京,而是在想方设法从细微处改变他所掌控的体制。
“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制造问题,”她说。“然后他们才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塔蒂亚娜·马卡罗娃带头反对她所在村庄及周边地区的新建筑群,她和邻居们与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一些人展开了对抗。

塑,里面有自己的教堂,气势十足的围墙上装有铁丝网。

瓦尔代湖的渔民。尽管这里是国家公园,但新的宅院正在侵蚀湖岸。
她和邻居们拍下YouTube视频,递交了正式投诉,并向媒体展示了那些新宅院如何侵占了湖岸——这显然破坏了这个国家公园的环境。走过据她说为了让村民远离湖泊而种下的多刺灌木丛,她带我们来到一小片湖滨,她说她的组织已经用行动成功让这里回归公共用途。
马卡罗娃坚称自己不是革命者,只不过是希望每个人都遵守法律。她说,更大的问题在于,因为这个国家的血腥历史,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害怕卷入政治。因此,没有权力的人很容易就被掌权者利用。
“因为他们家庭遭遇了那些巨大的灾祸,人们发现自己什么也决定不了,小人物什么也决定不了,”马卡罗娃说。“只要不干涉,你就能活下来。”
当我们离开马卡罗娃的家,我前一天就注意到的一辆灰色旅行车就停在几十米开外。它跟着我们驶离马卡罗娃的村子,当我们绕道穿过另一个村子时,它停在了主路上,随后继续跟随我们来到酒店的停车场。
沃罗涅日:生态时髦美学
普京得以保住权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俄罗斯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我们穿过莫斯科明亮的灯火,在沃罗涅日醒来,这是一个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俄罗斯流行文化中,它经常让人联想起首都以外地区的乏味无趣。

沃罗涅日是克里姆林宫雄心勃勃的城市重建计划的一个例证。

它正在用公园、现代游乐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来重塑单调乏味的城市。

政府官员仍然被认为是腐败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国家至少有一部分财富是在向下渗透。
“我总是想,‘偷吧,但也要为我们做点事,’”我在沃罗涅日遇到的一位45岁的老师尤利娅·利西纳(Yulia Lisina)说。“因为在90年代,感觉他们只管偷窃。”
在如今被秋千、光滑长椅、倾斜小路和精心维护的植被装点的苏联广场上,我在雨中走近一个打着伞独行的人。这名男子名叫尤里·马特维耶夫(Yuri Matveyev),今年66岁,他说他因袭击服刑15年后刚刚出狱。
他不打算在选举中投票。他说,作为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他觉得自己的观点没有被选票所代表。但他承认,城市的部分地区已经焕然一新。
“我们的高速公路不比德国的差,”他说。
即将重新开放的奥尔约诺利公园有一个木板墙面的建筑,蜿蜒穿过树丛,顶部有一个走道,里面有一个美食广场,后面有一个放户外电影的空间。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翻新工程肤浅的生态时髦美学是为了安抚那些向往西方的年轻中产阶级,否则他们可能会准备进行抗议。沃罗涅日的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在城市规划中复制西欧城市的感觉——但政治又是另一回事。
“民主是一种需要学习的东西,”在这里竞选连任的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安德烈·马尔科夫(Andrei Markov)说。“我们才学了30年。”
罗斯托夫:“普京就是一切”
但俄罗斯仍然存在着一些表面上的民主,克里姆林宫需要选票。为了见一见统一俄罗斯党最有前途的新选民,我在沃罗涅日以南约480公里的地方下了火车,坐出租车前往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
在煤矿小镇诺沃沙赫金斯克一家购物中心二楼的空气曲棍球桌旁,我发现一小群人在等政府办公室开门。他们中至少有五人是乌克兰边境上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分离主义地区的居民,他们是刚刚宣誓入籍的俄罗斯公民。
他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开设在线政府服务账户,这将允许他们在选举中远程投票。
“我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其中一名45岁的女性说,她只说了她的名字娜塔莉亚。“普京就是我的一切。”

分离主义地区的老兵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在乌克兰顿河畔罗斯托夫举行的纪念仪式上。

罗斯托夫地区的一所房子。普京去年简化了乌克兰分离主义地区的居民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程序。

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一个市场。
去年,普京简化了乌克兰分离主义地区的居民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的程序,并实际发放了数十万本护照,以加强俄罗斯的控制。统一俄罗斯党在该地区最知名的候选人是亚历山大·博罗代(Aleksandr Borodai)——他是2014年战争爆发后,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他的工作似乎是充实该党的民族主义势力。
“我们必须预期会爆发战争并做好准备,”博罗代上周表示,他警告称,与美国的冲突迫在眉睫。
2014年,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让他的支持率飙升。最近,俄罗斯国内对类似提高退休年龄等问题的担忧占据了舆论中心,普京的支持率已降至60%左右。但一些俄罗斯知名人士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普京在国内外采取更强硬的路线。
博罗代的一名助手帖木儿·奥克克特(Timur Okkert)同意与我见面,尽管他说我代表的是一份“敌对刊物”。他给我介绍了另一位归化的俄罗斯公民:亚历山大·盖迪(Aleksandr Gaydey),一名臭名昭著的前乌克兰叛军指挥官,他抱怨俄罗斯对国内反对派不够强硬。
一旦反克里姆林宫的起义开始,盖迪喝着一罐可乐发誓说,“我会第一个粉碎它。我会用力碾碎它。”
车臣:金钱的力量
最后一段火车旅行把我带到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普京大道上那些修剪完美的树篱前。这里的一些商店有裸露的砖墙和假的美国车牌,有叫“索伦”(Soren)这样的名字的咖啡馆,以及像“我们有滴滤(咖啡)”这样的招牌。政府大楼上挂着普京的巨幅画像,每个重要路口都有警察,人们普遍害怕批评政府。
这就是俄罗斯的未来吗?

车臣证明了金钱和记忆的力量能促使人们接受强人统治。

不到20年前,格罗兹尼还是一片废墟,它被二战以来欧洲最具破坏性的轰炸行动摧毁了。

克里姆林宫资助的车臣统治者拉姆赞·卡德罗夫今年将竞选连任。上一次,他以95%的投票率获得了98%的选票。

这与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经常在车臣取得的成果相似。
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在选举中最有名的对手是格罗兹尼前市长伊萨·哈济穆拉多夫(Isa Khadzhimuradov)。后者拒绝和我见面。我查阅了他的政党的格罗兹尼分部地址——该分部是为了维护民主假象的“体制性反对派”组织的其中一个——然后我顺便拜访了那里。
我在办公室遇见了75岁的地区党委书记马丽卡·巴拉耶娃(Malika Balayeva),她日常是教育工作者工会的一名雇员。她形容她的候选人哈济穆拉多夫“非常积极,非常谦逊”。
她会投票给谁?
“我当然会投给卡德罗夫,”她说。“一个人必须诚实,必须知道什么对人民最好。”
尽管如此,我还是听到了私下传播的不满和疲惫的声音,甚至有人猜测,尽管没有进行竞选活动,哈济穆拉多夫仍能获得相当大一部分支持。
我见到了少数仍在车臣活动的人权观察员之一,明凯尔·艾奇耶夫(Minkail Ezhiyev)。他说,“鉴于现实的某些方面,”有很多话他不能说。但他指出,俄罗斯绝对是难以预测的。他大胆地说,莫斯科上百万人突然进行抗议导致的后果可能会波及全国。
这让我想起,最近几周我反复听到列宁在1917年1月作出的预言,他说一场决定性的起义可能会在几十年后出现——预言作出的一个月后俄罗斯革命开始了——我也听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还以为它能够永远存在。
“我们有自己的历史道路要走,你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艾奇耶夫对我说。“你永远不会理解俄罗斯,因为它还不理解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