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美国来日本已经整整一年了。春天鸭川边的樱花,夏天热海的花火,秋天上高地的红叶,冬天北海道的积雪。到现在樱花又要开了,不知不觉中经历了完整的四季。
想过写点什么,但初来乍到,怕写出来处处显得没见过世面似的。熟悉了,却失去了提笔写的兴趣。一年时间对我来说挺久,但认识人多了,知道在这里住了二三十年的,在不同领域扎根很深的人大有人在,你观察到的和他们比,可能都是肤浅的常识,一年,又算什么呢?
对一个地方的感观,什么时候写合适呢?待的时间短了写不好,长了不好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内耗。如果需要一个由头,“一年”也许可以算一个,不长不短,不深不浅。
这一年,因为访问学者的契机,有机会去了日本从南到北 8 个不同的都道府县,20 多个不同的学校,从公立到私立,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文部省(教育部)“主流学校”到创新学校、“边缘”的残障儿童支持学校。因为我自己“伪学者”的身份,和日本优秀的思想者有深度交流的机会。再者,我一个人在东京带三个孩子生活,从区役所(政府)到医院、诊所、警察局、派出所、银行、邮局、快递站,衣食住行每个环节的生活都体验到了。而且,我在中国和美国生活各 20 年,在不同领域做过事,现在又是游走在日本的“老外”,保持了一个局外人观察这个社会的“特权”。这些加起来,也许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视角。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对日本的感受,“矛盾”也许是最恰当的。

▲ 《财新周刊》原文首页
矛盾一:无微不至与目中无人
前几天,一个美国朋友带着 6 岁的孩子来日本玩,暂住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
她们第一次来日本,所以我在线指导:日式的浴室怎么用;门口一堆按钮的用途;洗衣机为什么有一个按钮写着“洗澡水”;厨房炉子上烤鱼炉是个啥,刀藏在哪里;当然还有垃圾要分成 6 类,怎么分,怎么倒;在一个不大的两居室里,整齐有序地收纳着各种用品都隐藏在哪儿了?
小娃有点咳嗽,于是告诉她下楼走路 3 分钟内有药妆店;5 分钟内有便利店,两家 7-11,一家罗森;8 分钟内有两家百元店(我的最爱!),各种小餐馆。当然还有地铁公交,可以去到我推荐的各个地方。
朋友在视频那边大呼,哇,这么方便!
2023 年 3 月,我带着孩子们来到日本。一趟飞机,到了一个如此不同的世界,和美国西岸的农村生活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开阔静谧,一个接踵摩肩。无处不在的高楼大厦,成群的上班族,凌晨 5 点还在营业的居酒屋。与美国邻居开超级费油的大皮卡相比,东京的车都像被瘦身了的玩具车。这些场景与我曾经熟悉的工作生活猝不及防撞了个满怀,似乎无缝衔接上了被疫情隔断了的生活。当然,只是似乎。
孩子们没有我这样久远的记忆和对比。带他们坐夜间的百合海鸥线,电车在灯火通明的高楼大厦中穿行,海,楼,船,灯,迅速地交错着出现和后退,让人眼花缭乱,像是开进了一部科幻电影。而脚下,都是精美的小店铺,处处干净整洁,人人彬彬有礼。有时候我走过这些地方,觉得走过了一整街的蜡像馆,从人到商品到食物,都觉得不真实。特别是食物,我一直疑惑,日本食物这么精美,但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真实。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 因为日餐不“飘香”,色香味——眼见有色,入口有味,但少有弥漫的香气。
回想一年以前,初来乍到,看什么都新鲜。从厨房里可以自己站立的案板、便利店里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到超市里一人份的蔬菜、百元店里清理各种角落缝隙的小工具……当然,还有洗手间里安装的加热冲洗马桶坐垫!
那时候我也常常“哇!”,但当地的朋友总是一脸茫然——全世界不都是这样吗?不应该就是这样吗?只一年的工夫,足以让我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了,我也以过来人的平静,面对朋友吃惊的大呼小叫。
日本在很多地方都能体现出对人的无微不至。第一个层次,无微不至的产品设计。在日本社会,特别是消费品设计,吃喝拉撒睡每一个细节都有超级人性化的产品,而且设计制作非常精美,赏心悦目,方便实用,经常有你想都想不到的巧思。比如,我在 7-11 买的咖喱饭,说明上提示,把盒子折一下便可以当成架子,放在微波炉里加热时,架子形成的角度能够方便蒸汽散去。

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数不胜数。我想我要是学产品设计,在日本肯定每天都体验到暴击的感觉。
第二个层次是无微不至的体检和医疗。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各种关于日本医疗体系的人性化和先进,从体检到牙医、儿医、急救、手术都是无微不至。我记得一个诺言社区的朋友说,爸爸从上海来日本看病,医生和护士很重视病人的体验,他们会鼓励病人如果疼的话,要说出来。即使住院,也受到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整体的感受温暖舒适。但是另一方面,看到一个分享,说在妇产科医院,哪怕没有麻醉,日本女性生产都很安静,都不喊的。而不喊肯定不是不疼!这也是一个矛盾吧。
第三个层次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型政府。去区役所办手续,所有人为你服务都勤勤恳恳,一丝不苟,态度友好。如果表格有点不符合要求,他们也会尽量给你想办法,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利为难他人。一个小例子,作为外国人,会拿到一本有英中日韩文的厚册子,里面从急救到垃圾分类、从社区服务到免费查体,都写得清清楚楚。
但另一方面,说日本又“目中无人”,你可能会很惊讶,怎么会?为什么?
我的孩子们在美国学校的校长是一位日裔美国人,她是成年后从日本到美国的。我去年跟她说我要去日本,本以为她会非常自豪地向我介绍她的国家,没想到她反问:“你为什么要去日本,去这个压抑灵魂的地方?!”我和她聊了才知道,作为一个对事业有追求的女性,也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在日本社会是多么被“看不到”和受压抑。那之后,也才读懂上野千鹤子老师书里描述的日本女性,面对的是多年未改善的多重结构性困境。
根据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GGGI)中关于性别平等指数,日本在 146 个国家和地区里排名 125,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中国排名106)。从入学到就职到报酬到晋升到社会福利,社会中对女性的结构性不平等无处不在。日本社会的另一种“习以为常”,就是对女性的目中无人。
在诺友群里有一个人问:朋友的孩子 15 岁,想去日本上学,有没有可能?群主回复:我得先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才能回答这个问题。男孩可以考虑男校,女孩就没有那么多选择。如果进男女混合的学校(比如一些大学的附属中学),女孩要比男生成绩高很多才可能获得与男孩同样的机会,而且这在日本已经是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实。男校有着明显的优势。2022 年东京大学新生录取人数,排名前 20 位的学校中,有 14 所男校。如果能进入某些男校,被东京大学录取的比例可以高达 50%。
日本顶尖名校女性录取比例非常低。像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样的“好学校”,女性的录取比例在 20% 左右,这其中也包括了文科专业,事实上,理科专业女生比例只有 10% 左右。你可能说这是理工科的大学,女生比例低很正常。但是放眼世界,同样是理工科大学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女性录取率已经到 47%,哪怕是中国清华大学,女性也占到了 35%。
在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国家里,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的毕业生中,日本女性比例是最低的。以至于一位诺友说,在东大的饭堂吃饭,感觉像进了男生宿舍。
2018 年前后曾爆出丑闻,有十几所大学通过暗箱操作,刻意压低女性考生的入学分数,使她们无法被录取。虽然这几个案例得到曝光,涉及的女生也得到了赔偿,但是到 2024 年,在入学考试中,女生要获得比男生更高的分数,依旧是社会默认的共识。更可笑的是,如果女孩被东大等名校录取,会因为太聪明而找不到夫君,也仍是社会共识,在日本社会中,女性的主要角色是在家中相夫教子。
2024 年 3 月,美国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凯蒂·布里特(Katie Britt)在拜登发表国情咨文之后,为了能吸引女性选民,在厨房里以一个“在家女性”的形象作了声情并茂的反驳演讲,结果因为“以 60 年代女性刻板形象出现在厨房”,遭到美国从左到右的群嘲,以至于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做了一个模仿她的表演,一时火遍全网。而在 2024 年的日本,这种女性居家的社会角色不仅不会受到批评,反而备受推崇,差距令人惊叹。

上面说的只是学生,大学女性教授的数字就更低了!虽然号称“逐年升高”,仍然连 20% 都不到。
所以,一方面日本是民主宪政国家,有服务型政府、发达的服务业和市场经济,而且在 1985 年就通过性别平等的立法;另一方面,在教育方面对女性的明显的不公平是广泛的社会共识,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矛盾二:儿童友好与教育畸形
日本是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典范,如果你一早出门,会看到人行道上、地铁站里、公交车上,很多六七岁自己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即使生活了一年,每次见到这样的情况依旧感到震惊。
大家可能也都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过日本的幼儿园和小学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视,从各种生活能力到户外运动,而且这种教育由来已久。我去离东京新干线车程 6 个小时的山口县萩市,在那里的明伦小学校旧址,看到 80 年前的学校运动会。男孩女孩都光着脚在土操场上奔跑跳跃,参加各种比赛。
对身心有残障的儿童,教育配置更是令人敬佩。家庭基本可以免费让孩子得到很好的照护和教育。我在东京访问一个给残障人士提供支持和服务的机构,校舍是以前的小学校改造的。在这里“工作”的残障人士,他们制作饼干并售卖,饼干的配方是著名的餐厅所提供的。这样,他们既可以创造提供、获得收入,又促进了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并宣传了“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理念。我认识的一位就读于设计专业的博士,研究的内容是重病儿童患者的特殊衣服,孩子可能需要在不同的身体部位插管,如何在满足功能性的前提下让衣服好看、孩子爱穿。有这样的专业和行业存在,就让人可以管中窥豹,知道这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之完善。
这样的体系,首先需要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另外需要社会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支持的共识。有了这两个前提,还要有足够多的专业机构和公益组织。
作为曾经的母乳妈妈,我看到日本随处可见的母婴室也倍感温暖。在商场、火车站、博物馆,我见到全世界设备最齐全的母婴室、哺乳室,里面有给吸奶器消毒的机器,有热水,有舒适的沙发。公共卫生间都有放小宝宝的安全座椅,方便带小孩子的妈妈如厕。






日本的森林学校,自然教育也是世界一流。一土学校和日本的自然学校也有常年合作,从他们的机构和老师身上都学到很多经验。
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的孩子,日本的教育又存在非常畸形的一面。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内卷”,以至于专门有一个词叫“教育虐待”。
2023 年 3 月,一名家住佐贺县鸟栖市的九州大学一年级学生,将自己的父母杀害。原因是他常年遭受父母的教育虐待,只要犯错就会被狠狠责骂,如果成绩不好,就要跪着正坐一小时以上听说教。即使他做完作业才去玩儿,也会遭到父亲的斥责。由于承受不了常年遭受的教育虐待,这个学生用刀杀死了自己的双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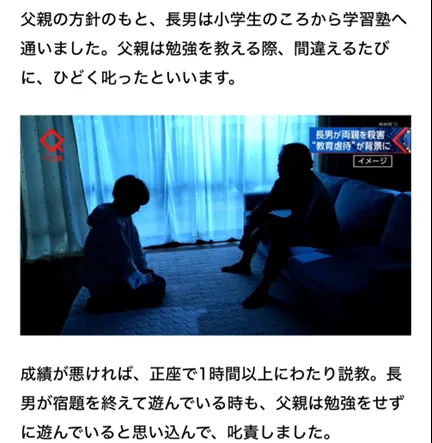
“教育虐待”一词,是 2011 年由日本儿童防虐待学会提出的概念,指借由教育之名,给孩子施压造成伤害;让孩子超过最大容忍限度地学习;无视孩子的意愿,在成绩和未来出路上过分干涉等。社会还对“教育虐待”和“教育热心”的区别进行了广泛讨论,使成人清晰地了解两者的不同:
——教育虐待:将孩子视为自己的作品;孩子和自己的成功非常重要;自己觉得是好的,就坚信不移;
——教育热心:认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关心孩子是否快乐;一条路行不通,会选择其他路径。
201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指出日本的教育制度竞争过于激烈,学校环境压力过高等问题,并警告社会的竞争性会损害儿童的成长。
教育虐待的影响是长远的,童年受到教育虐待的孩子,即使成年了也会有 65% 左右还在接受治疗,有的甚至会患上“复杂性创伤性应激障碍”。所以,这样“卷”,社会和个体都付出巨大的成本。
我看日本这些数据,会有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数据相当糟糕;另一方面,至少有数据,而且数据非常翔实,也有报道,有媒体曝光,有正常的公共讨论。这也是情况变好的必要条件,虽然远不是充分条件。
我采访过一所位于东京旁边的普通公立小学,问老师有多少孩子是在学校之后上私塾(补习班),老师一声叹气后说,80%。
你可能和当时的我有一样的问题:日本公立教育这么好,为什么要上补习班?
如果能考入重点私立中学,那么升入著名大学的可能性就很大,进入大企业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大企业很大程度是不成文的终身雇佣制,随之而来的社会认可、福利等等加起来的红利,是差学校毕业生终身都无法超越的。
所以层层倒推过来,孩子需要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课外补习,为了占坑,很多家长在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就送孩子上补习班。有的甚至更早,幼儿园大班就去参加考试。学生放学后,回家稍作休息,晚上 5 点半到 8 点在补习班度过。自己带着晚饭,课间热饭吃。
我假装家长去过一所顶尖的补习班。中午过后,学生还没到,我问能否看一下教室,工作人员允许我看监控。看到监控的一瞬间,我脊背发凉:五六个屏幕,每一个对着一间教室,每间教室没有窗户,没有装饰,只有白墙和整齐的桌椅,像个大号的牢房。从环境设计看,根本不应该是为孩子设计的。
补习班的工作人员身穿黑色西装,打着领带,显然就是一个工业产品。正如大量中国家长熟悉的,他们有许多方法,让家长和孩子因为焦虑而买课。补习班每月考试,按照成绩调座位。为了保持成绩,孩子不仅平时的晚上要上课,甚至连春假、暑假、寒假都要参加补习,以实现“赢在起跑线上”。
这是“教育虐待”产生的社会结构问题。
日本社会有很多讨论,也有小说等作品反映了过度竞争对孩子和家庭造成的伤害。补习班不仅学费昂贵(补习班一年的费用相当于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而且孩子苦不堪言,也会衍生出青少年旷课、抑郁、校园霸凌等问题。
2023 年夏天,我和《教育市场化的边界》的作者塞缪尔·E.艾布拉姆(Samuel E.Abrams)专门讨论这些现象产生的社会规则和政策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观看直播回放。
另外一组数据也值得关注。在日华人占日本总人口 1% 左右,但是在某顶级补习班,华人的孩子占到了 25%。对中国人来讲,日本的“卷”再糟糕,肯定比不上国内,所以很多中国人第一反应,哦,“卷”啊,我们熟悉啊,擅长啊,比你日本人还会“卷”呢!但是,如果是为了“卷”,为什么来日本呢?何不留在北京黄庄“卷”呢?如果把日本“卷”成了黄庄一样,是自己想追求的吗?
当然,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害者,体系问题不解决,很多个体是没有资源对抗的。
但是,哪怕在这样的环境里,有选择么?答案是,永远有。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