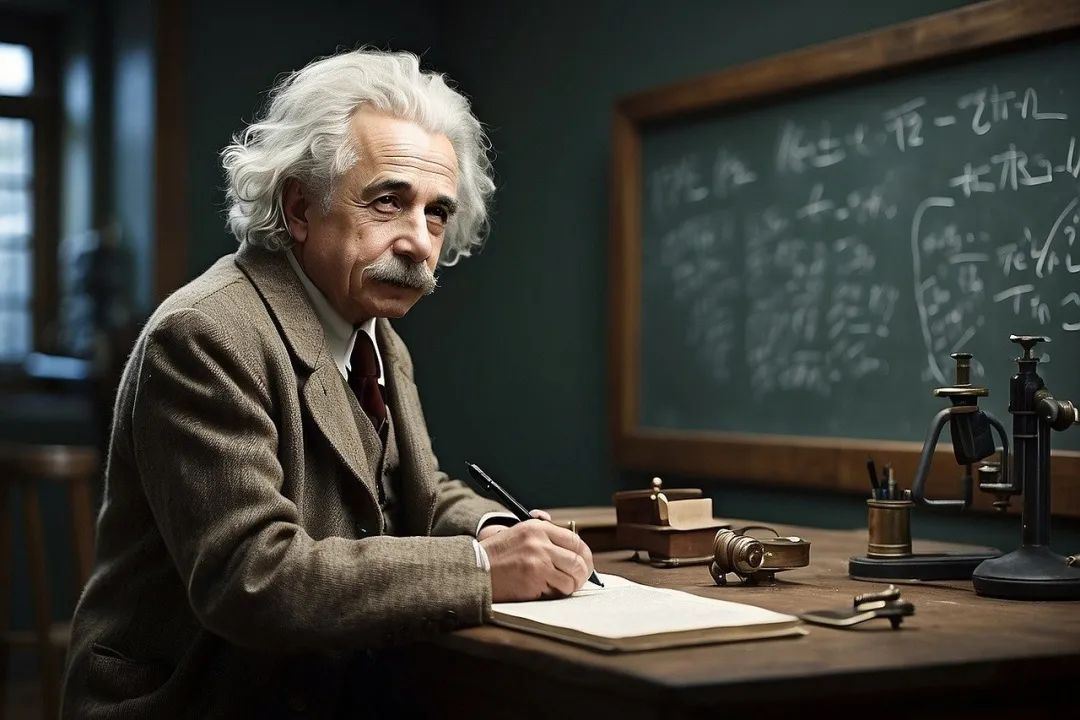
最近在执行中国科协项目“科技人员参与公共事务研究”,收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反馈。一位科学家朋友说,作为科研工作者,参加最多的公共事务其实还是科普,但相比于科普一词,“参与公共事务”让人尤其觉得有自豪感。
为何科学一定要被科普?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科学在展示公共性方面有着超越其它种类知识的需求。不论是科学在古希腊时期的萌芽,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勃发,都离不开其向公众广泛的宣示。比如科学史上广泛流行着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因为观察星空而不慎跌倒,遭遇周围人嘲笑“泰勒斯总想着观看星星,却忘了脚下的坑”时的回答:“总是看着脚下的人是不会仰望星空的”。这句伟大的广泛流传的名言其实值得重新把玩。观察脚下的坑恰恰是人们行进时的常规状态,而观察星空去寻求自然规律却不是普通人在自然状态下的需求。这也导致了要让人们像注意路况一样关注星空,那就必须要有格外的努力,让他们能仰起头来。
正因为如此,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先贤们,从一开始就努力向公众证明,这种寻求自然普遍规律的工作,是对公众们有利的,是符合道义正当性的,是无私利的,用今天的话,也就是具有公共性的。而有意无意地,公众的形象也就成了那些如果不被启迪,就总会只看脚下道路而不会仰望星空的人们。当然,不同年代的公众代表着不一样的群体,古希腊的公众不包括奴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公众当然是有了一定知识的市民阶层。
面向这样的市民阶层,伽利略要登上城市最高点比萨斜塔来宣示自己发现的重力原理(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越重的物体落得越快的原理的错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波义耳要把自己发明的空气泵拿到大街小巷去展示来说明实验科学的重要性,并最终在人们对真空状态带来的神奇效应的赞叹中,战胜了与之辩论的霍布斯,为实验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后者眼中的科学,则是展示秩序和规律的数理研究。
其后科学发展史也不乏各种各样的展示。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普已经成为科学的必然组成部分,而通过科普要向公众展示的,就是科学对于促进公共利益有极高的价值、且不是为了私人获利这种公共性。一代代科学家一直把这一点奉为圭臬,社会也日渐接受了这种说法。
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本身不具有公共性,需要通过科普来建构。而是强调,科学的公共性价值,在其发展的早期,必须要通过科普来展示。在二战让科学大放异彩之后,科学的公共价值又进一步通过支撑决策来体现。正如泰勒斯的例子所表明的,从科学萌芽的古希腊到科学勃兴的近代,科学知识和科学规律都不是日常生活甚至不是知识阶层的日常知识生活的常规组成部分,都需要积极地进行传播。正是这样的动机,让一代代的科学家们一直把科普当成自己的使命,这不仅仅是因为通过科普,公众能获得科学知识,也是因为,通过科普,科学造福社会的公共性理念能不断被传递,其权威性也相应地日渐提升。可以说,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科普(以及后来科学被应用于支持决策等其它公共事务的工作)是科学作为公共性知识的内在组成部分。
科学专业主义的兴起对公共性的挑战
然而,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专业性科学知识生产日益崛起。促进科学这种专业化发展的首要原因,当然与科学知识生产本身越来越精密,越来越不可能仅仅靠单纯的思考或直截了当的尝试来实现,当然也越来越难以直接展示给公众。但这并不是阻碍科学通过科普展示其公共性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科学自身越来越建制化,越来越不需要通过向公众展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科学家们越来越依靠于同行的评价而不是社会的认可。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指出的科学的四大规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 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 有组织的怀疑(Organized Skepticism)——可以说,既反映了科学具有公共知识的特性,也说明了科学界自身的专业化,让“有组织的怀疑”这一体现科学专业性特征的规范越来越成为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流特征。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已故的著名科学传播学者Sharon Dunwoody 引述了一个出现在二十世纪早期的例子——原本对新闻界非常友善的美国科学界,开始出现了某学会成员因为自行接受媒体采访介绍其未发表的成果而被所在学会谴责的例子[1]。Dunwoody提到的例子的发生时间与默顿提出科学的四大规范的时间(1942)相隔不远。它们并非表明科学不再追求公共性了,而是说,在科学家们看来,他们所追求的造福于人类社会的公共性,不再只需要通过科普来获得社会公众或媒体的认可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反对越战、环保运动、反核运动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抗争越来越质疑科学的权威性、合法性及其对社会的公共价值,从而导致了西方科学界猛然意识到,需要通过科普和其它社会公共事务,来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支持。虽然科普重新得到了科学界领导人的重视,虽然科学家投身包括科普在内的公共事务重新开始受到褒扬,但科学自身的专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同行评价超越公众认可的趋势已经覆水难收了。
作为后来者,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当然不尽相同。但从赛先生与德先生被并列当做救国法宝开始,中国的现代科学从起步阶段也承载了救国救民的公共性。二十世纪初诞生于康奈尔校园的中国第一个科技社团中国科学社,其迁回国内后首要的任务也是从事科普。在新中国成立后,科普也与扫盲一起承担起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公共任务。在文革的大破坏之后,与“科学的春天”一起回归的,也同样包括能让《湖南科技报》发行量上百万的科普热潮。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科学研究的专业化,也同样让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数量日减。
如何在专业化日盛的时代
弘扬科学的公共性
无疑,当专业化让同行评议成为科学家工作的金标尺的情况下,他们从事科普和其它公共事务的动机自然有所减弱,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同行评议作为主要专业标准的情况下,科普难以为个人赢得足够的回报,更是因为科普收获的社会好评可能会僭越了同行评价。上文提到的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科学家会因为向媒体推介自己未发表的研究而受到所在学会谴责就体现了这一点。我在给科学家做科普报告,强调其重要性时,也经常有科学家会声称,不是他们不愿意做科普,而是因为担心科普造成的公共显示度会影响同行对其的认可。
然而,说专业化逆转了科学家的科普意愿却言之过甚。科普以及科学家基于专业知识参与的其它公共事务为科学的公共性提供了背书,并早已内化成科学家的一般性信念。我做了多次科学家科普行为调研,没有任何一次调研,认可科普重要性的科技工作者的比例低于90%,不论被调查者是否实际从事过科普。
基于科普具有的对维系科学公共性形象的内在价值,经过多年摸索,西方科学传播界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包括禁止论文发表前进行宣传的Embargo制度,包括在对科研成果进行报道的科学新闻中引入同行评议等等。在科学家(特别是青年科学家)从事其它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做法,比如科学大使制度,把青年科学家派往社会组织;比如国会科学研究员(congressional science fellow)制度,把青年科学家派给国会议员做助手,在帮助后者进行科学决策的同时维护科学界的利益。这些举措都在确保尊重科学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和专业性的基础上,维系和延伸了科学的公共性。
自然,中国的科技副职、科技特派员等制度也属于这一类型。虽然相对而言,科技副职和科技特派员主要做的工作是科技扶贫、科技促发展和技术转移而不是科普,但它们发挥科学的公共性职能的诉求是一样的。
但是,不论是弘扬科学的公共性还是凸显其专业性,都需要时间。就个体科学家来讲,即便从事包括科普在内的社会公共事务不会有违科学的专业性,但终究要消耗时间。这种矛盾,在当今很多科研机构把科研绩效与奖金挂钩的情况下就更加突出了。
老实说,单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在科研绩效与奖金挂钩的情况下,很难得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无论科普和其它公共事务多么重要,在对科研产出进行数目字管理的情况下,它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超过科研本身的权值。然而,当我们回归科学所具有的公共性本质时就可以发问,用工分来计量科研产出真的合理吗?用工分计量出来的科研产出,是更多鼓励公共知识的生产呢,还是更多地激励科研工作者来生产主要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的知识?
而回归科学的公共知识属性,我们则可以看到,通过科普和其它公共事务促进科学造福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维系科学的公共性,这与科研同等重要。科普与创新同等重要的“两翼说”在维护科学公共性这一点上,也同样能找到注脚。这么说,并非意味着科普比科研本身更重要甚至可以取代科研的位置,而是说,当我们致力于维护科学的公共知识属性这一点时,我们就有更大的可能性和空间,来妥善处理科学与科普之间的张力。
因而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中国的科学能超越行政化的科研数目字管理,真正回归到创造公共知识的本源中。我们期待着这样的举措不但能唤醒科学家心中的公共服务心,也能促进他们以多样化的方式投身其中。
参考文献:
[1]Dunwoody, S.(2021). Science journalism:Prospects in the digital age.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3rd edition)(pp. 14-32). Rout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