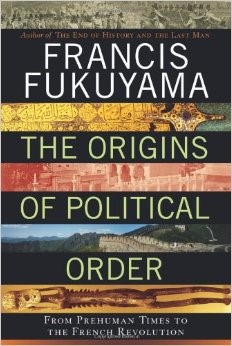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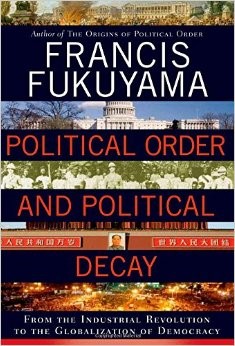
上卷,2011年三月出版,608页 下卷,2014年九月三十日出版,676页
著名政治学和社会历史学家福山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终于在九月底出版了,此前一星期得到了它的电子版,先阅为快,觉得果然不同凡响,很值得引介。这是福山的大制作的下卷,上卷《政治秩序的起源》在2011年三月问世。三年半的时滞,颇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在上卷的自序里,作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下卷呼之欲出。而各界翘首以待的,自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想知道在(后)现代世界的体制建设到底将走向何方这个大问题上,福山要提出什么样的指引?
上卷《政治秩序的起源》只是某种铺垫,从它的副标题——从史前文明到法兰西大革命的演化,便可以知道,福山着力回溯先前的历史沿革,乃旨在解析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条件、所处的态势、和面临的问题和抉择。其中最有价值的,也是作者致力从各家的纷纭诠释中脱颖而出的贡献,是要指明现代人类进展,鹄的究竟在哪里,怎样避免因为人类社会的错误选择而陷入僵固、瓦解、沦丧,即他及其恩师S.亨丁顿的“政治秩序的衰朽”。因此,下卷的副标题——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制度的环球化,表明了其论述范围与我们所关注的利益、情感、展望的关联更为切近。
两人所说的“衰朽”,以笔者的理解,自然不止是政治的,也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的秩序,以国人习惯的用语来说,是“精、气、神”的全面衰朽,只是比较显著地表露在“政治秩序”——人们角逐最外露的竞技场上;而他们所说的“体制”安排 (institutions building)——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石和赖以更替的驱动力,也不限于成文的法规以及不成文的习俗和潜规则,而是包罗广泛人群的“稳定、有价值的、在反复运行着的行为模式”("stable, valued, recurring patterns of behavior")。据此我们不难明白,福山要处理的框架是多么恢弘,信息有多么庞杂。他的这两卷书也表明了他的关注和器识也的确能称配得上这个应战努力。福山的研究,除了他专精的比较政治学外,涉及到了人类学、演化心理学、宗教史学、经济史学等多种门类的学识。而他的主导观念思路,较多地师从S.亨丁顿、W.威尔逊、F.黑格尔、M.韦伯、E.涂尔干等大家;而扬弃了T. 霍布斯、J.洛克、J.卢梭、J.穆勒等人的传承。
在探究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如此发生?人们长期演化和积淀而来的本质条件是什么?与当今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在互动的?它们教会了我们什么?对人类社会未来的进展又有何预兆…… 这些大问题时,福山认为,后者——霍布斯、洛克、卢梭、穆勒等对人的原初就是有能力独立做选择的自由个体,而后才被迫加入某种形式的团体,参与有限度合作的假设,虽然不无高尚的憧憬,却是过于理想化的观念: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如此“自由的个人”(free agent),哪怕在初民的草莽时期,从来未曾存在过。而以这样的假定为出发点所做的演绎推理,诠释以往体制的成型进程并推测未来体制的走向,也就很不靠谱了。除了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来审视历史实际发生过的演化过程,福山多方借助了亨丁顿的分析框架来提出自己的诠释。在书中他不但引用亨丁顿的学说不下百来处,而且在书序和结尾语里还加以长段的阐发。
同福山爆得大名的第一本著作《历史及人的终结》(1992)的论述,本书显然是大异其趣的。在那本论著里面,振奋于柏林墙的倒塌,福山宣称,冷战的结束不只是一场竞赛的结束,而是人类在意识形态演进的告终;就此意义,是历史的终结,判定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将是人类政府治理的最终形式。这种乐观预断,以及他对后现代主义中过度崇尚个人旨趣以至于社区意识空洞化的评判,把福山推向世界前台,成为众所热议的公知人物。然而这一切有了全然的改观,尤其是近十年来,即使福山自己不是很乐意明确坦承的。福山曾是美国新保守主义门派的创始干将,却在2006年同新保守主义割席绝袂;从极力敦促伊拉克战争输入美式民主体制,到大力反对小布什总统的全球战略,福山几乎可说是判若两人。这十年来的变化,驱策福山循着亨丁顿开拓的思路从事新的探索。是纷呈的各种矛盾给他带来了新的观察,还是他的心智有了丰富或蜕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本文评述的这两卷巨作,是福山新探索的成果。
福山在本书的上卷建立起框架,来解释政治秩序(着眼于国家和政府治理,也包括社区的治理)的体制(institutions)的源起和发展,怎样的体制安排才能导致良好的治理,以及为什么一些国家持续兴盛发达而另一些国家迅速陷于衰朽混乱,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福山把良政美序的治理归因为三个要件(或支柱)的平衡,缺一不成:1、强大而富有成效的国家(a strong and effective state);2、按法规治理(the rule of law);3、执政者对治下民众的尽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他认为,在欧陆的历史上,率先达到治理规范的主权国家的政府有英国、丹麦、瑞典等,俄国只满足了要件1,法国、西班牙只满足了要件1和2,而匈牙利、波兰等国则满足了2和3。
福山认定,缺少了要件1,强大的国家是政治秩序的基础性支柱,就谈不上在一个地域实施治理的主权和秩序,居民也无从得到安全保障、基本生活秩序、以及基本公共设施和服务。在这个基础认识上他有类似霍布斯的见解,认为无政府主义或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所主张的,能够充分自行其是的个体就可以结成有效的合作联合体,只是某种奢想。当政治权力松垮孱弱,处于真空的局面下,社会秩序无法形成和维护,个人自由根本无从确保,至多是得而复失而已。
但是,要件1还远远不够。不具备要件2和3,强大的国家难保不滥用权力,沦为小集团(或世袭家族)的利器,来侵害和压榨它原本应该服务的治下人民。治理和秩序很快趋于溃败,就像中国的秦朝,不出二世,天下与之皆亡。秦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突破家族和氏族藩篱的国家治理,但由于要件2和3的难产,中国的文明兴衰更替,始终走不出怪圈。而与之对照的,印度虽说有了适度的法规治理和公权力问责,但因为建立不起支柱1,也始终是乏善可陈,徒令世人叹息。
可见怎样使得三个要件制衡而能和谐,要件2和3既能有效地制衡要件1,将其纳入公权力的合理框架不致滥用,又不削弱要件1的治理能力,是人类世界的大难题。三个要件怎样取得平衡——就要件的本质,相互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对峙的关系——是福山探索的关注点。而他的论述以及援引的各类历史案例,正是本书的精彩看点所在。
长期以来中国的儒家和法家的争论,王霸之术杂糅的困境,儒表法里辩难的摩擦,一直贯穿着我们的治理体制;西方的王权和教权(主要是有组织的天主教会,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教会变革)的拮抗,企图把世俗的权威隶属于一整套被神圣化的规则之下的努力,则绵延了千余年。具体的社会和政体形式尽管多样,目的却是一致的,政府再怎么强悍,不论由家族、势力集团、还是由民选的精英来主持的,都必须服从法规。然而,这套法规来自“神授”也好,得自“天意”也罢,都无法自动地长期奏效。要件3,对公权力的问责,不得不靠民众自己来实施。人们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来委托给政府集中使用,这样的信托关系能否如初衷所愿地得到切实履行,责任却还在治下的民众。只有在滥权得到了切实地惩罚,腐败和低能的官员得到了切实地罢免,恶法被切实地废止,错误和失效的政策被切实地纠正,“天意”才得以伸张和施展——迫使政府“履约”的责任是在民众身上。以福山的结论性意见,任何“天赋”或“天然”的权利,只是取得了“法规高于一切世俗权力”这样超越性信念的人们赋予他们自己的。世界上各个人群在国家治理的效果上的差异是如此之悬殊,非常关键的因素在于人民和精英代表是怎样互动的,他们是怎样进行政治参与,怎样参与到更广义的合作(譬如市场的交易活动)中来的。这这件大事上,人的责任义务是无从旁贷的。
在这两大卷书里,福山对中国有着突出的关注。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中国的历史模式和并评析了眼下的问题。(在上卷的封面里有长城的图景,在下卷的封面里这出现了天安门城楼。中国的传统模式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和朝鲜。)福山指出,在建立基本的政治秩序上,汉文明有过非凡的贡献,秦始皇建立了人类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的统一帝国,并领先世界一千多年突破了家族和氏族的局限,建立起科层式的吏治。这种精英官僚体制若能有效运作,可以向社会提供秩序、安全防卫和基本的公共品服务。但是,它不足以制约皇权,尤其是皇权僭越、滥用公权力的时候。假如说“口衔天宪、举步为法” 的君王,握有绝对权力,有时尚能给臣民们带来基础性保障的话,诸如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等等,那么遇到孱弱乖张的“坏皇帝”——出现的概率通常更高——人民就得遭殃。此时诉诸礼教道德的儒臣就束手无策,根本没法钳制。特别当外族入侵、自然灾祸交相煎逼的关头,整个社会秩序溃散,王朝国家就崩解了。强盛的集权国家堕入到万众涂炭、千里赤地的惨剧,周而复始不断上演的原因,按福山的说法,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治理虽然也按法规办事(rule by law),但是始终不能上升到真实的法制(rule of law)。换言之,始终缺少强健的要件2 和要件3这两根支柱,法规仅仅用作统治的工具,只是下级官吏必须服从上级官吏的规矩,而不能成为治理正当性的内在来源。
福山认为他的模式,即持久稳健的政治秩序需要三根支柱相得益彰地支撑,具有普适性。他的理由,是人类的共同先祖从非洲走出来,演化的阶段大致相近;各人群为了生存和发展,所要处理的问题、所需竞争的资源、必得响应的挑战也大致相仿,尽管所处的环境差异显著。而且各文明处在相比较而存在的态势:问题解决得如何,有没有成效,不仅是你应对挑战的能力是否差强人意,而在於你响应挑战的成果是否优于同你竞争的其他人群和其他文明,不然的话你就会在发展的进程中遭到淘汰。因此我们不得不汲取他人的经验和教训,不然难以保持自己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