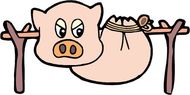说人胖得像猪,骂的人和被骂的人,往往都不生气,若是杀了有肉吃,更是皆大欢喜的事。
总场张场长,很胖,坐镇我们水利指挥部,真是好事不断,逢法定假日,大家有肉吃,即使传统的节日也要吃。更令人常常兴奋的是,这一条渠的开工,阶段性的完工,也要杀猪庆贺。指挥部食堂两口大猪,还不到年令就贡献了。那么多的喜兴成就怎么办,张场长批条,到农队、牛羊队去要,全场支持水利嘛!再说,修水利还不是为了你们队。不要说指挥部食堂也给钱,(比内部供应价还低)。大多数的队可都是敲锣打鼓用马车送来的。我们指挥部的人,说是工作辛苦,都累瘦了。可遇到多年没见的朋友,都瞧着我们说胖了,胖的像猪。于是说的听的都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东北虎,逮着猪就可以吃。我们得先把它杀了。终于轮到我当了一回刽子手------天地良心,只是帮凶而已。
那天,管理员套了小炮车,我正好完成了西三渠的测量,闲着没事,便拉我一起去近处的农三队,执行场长给的任务,拉回一头猪来。农队长一听场长圣旨,马上从猪圈里诱出一头200来斤的大母猪,回头交待会计记账,“指挥部拉去50斤小猪一头,单价4角5分。”若真是50斤,加上我们俩大男人,小炮车是装得下的,可确确实实是两百斤,即使绳子绑住了猪老兄,它也不安分的,只要动一动,也会把我挤下来;管理员是无碍,他坐在前头,有一条宽的木板好坐,来时我是坐在边沿,五公分,又没把手,一路担心,几次要掉下去,便索性坐在车中,把军大衣当坐垫,倒也舒服。此刻多了猪老兄,便没有了放屁股之地。
有它没我,有我没它,“把它杀了!”农队长一听,求之不得,唤来几个阶级弟兄,把庞然大物拽了下来,抬上一条带有血腥的大木凳,这时猪老兄开始嚎叫了,晓得命没得了,我想用什么去堵它的嘴,最好是什么手帕毛巾之类,却被农队长挡住。“叫你个球!”农队长将长长的尖刀,从猪八戒突出的长嘴捅了进去,这猪几乎没有经历由强变弱的过程,血流了一地。那里人是不爱吃猪血的,他们说麻烦。
猪死了,农队长说好事做到底,将猪毛剃了,吩咐他们的食堂把开水挑过来,倒在木凳旁常年备就了的一口大锅里。嫌锅里水不够热,便在锅下灶膛丢几根木材,烧着了,“死猪是不怕开水烫的”。一直在边上的他们食堂胖大师傅此时插手了,本来杀生是他的拿手,不就是让队长逞逞能;可这吹气的玩艺非我胖大师傅莫属。他用尖刀在脚蹄上划了一个口子,伏下身子,用自己的嘴对准那口子吹,刹时猪的躯体胖起来了,肿胀起来,到比他身躯还胖时,他用绳子将口子扎紧了,黑黑乎乎大大一团,被四个人,其中就有我这个门外汉,不遗余力地,沿着锅边,轻轻放下去,翻滚的开水立刻平静了。胖师傅指挥我们,上下左右翻动,又一声令下,我们齐齐把猪抬将起来,放至木凳上,扶着。胖师傅拿起一把铮亮的铁片,像理发员给男人修面刮胡子那样,将猪毛褪尽,随后,中间剖开,说是内脏里面叫我们自己去弄,说是张场长喜欢吃猪大肠的。猪蹄就留下吧,这是规矩,队长和大师傅喝酒时的规矩。
灌洗肠子要费时间的,回去慢慢弄吧。我们把光溜溜圆滚滚的胴体抬上了小炮车,我垫了一块纸板坐在胴体上,像坐在沙发上,惬意极了。
几年后,什么都开放的年代,有些城市的文人说是看着女人的胴体,美妙极了,我不说他没去过农村,不知道动物没头没脚的,死了的才叫胴体,要知道没头没脚少女称胴体还不把你昏死过去。
因为想着猪肉好吃,结束也是生命的,感情上没有什么。可怜的猪临终时受惠人,一滴眼泪也没有。心理学家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