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自然》官网刊登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以更好的方法衡量科研人员的流动性,进而评估这些政治行为的影响。
最近西方世界弥漫不散的政治动荡,让科学孤立主义、不热衷合作、流动性减弱等趋势抬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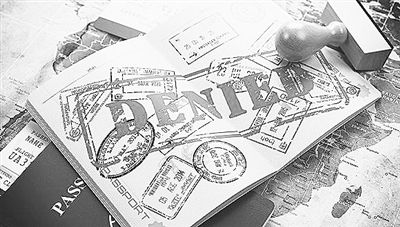
上个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布了一年之内的第三次旅行禁令,不允许特定国家的人进入美国,还对更多类型的签证进行限制。这些命令阻碍了滞留海外的学者和在国内从事国际工作的人的自由流动。
再往前看,3月份,英国首相特里萨·梅开始正式切断与欧盟的关系。英国机构面临非驻欧盟科研人员的潜在流失局面,还将花力气破除藩篱,以顺畅地参与欧洲联合科研项目并获得资金支持。
日前,《自然》官网刊登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以更好的方法衡量科研人员的流动性,进而评估这些政治行为的影响。
样本量浩大的细致“摸排”
印第安纳大学情报学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卡西迪·R·杉本课题组发布的这份报告,基于对科研人员全球流动性的分析,试图揭示科学体系受到的影响。
虽然科学人才的规模和组成通过国家调查和注册机构已经十分成熟,但了解科研人员的流动频率、他们去了哪里、形成了哪些网络,以及其流动对科学工作的影响非常重要。
课题组的分析数据来自于2008年至2015年间1600万名独立科学家发表的1400万篇论文。其中,96%的科研人员只有一个国籍,他们属于非流动人员。大约4%(超过59.5万名科研人员)是流动人员,他们在这段时间内有服务于多个国家科研机构的经历。结果显示出惊人的趋势:欧洲和亚洲的科研人员流失严重,而北美入境科研人员则大幅增加。
“大脑流通”影响力不容小觑
此前有假设认为,欧亚流出科研人员以牺牲原国籍为代价,换得了流入国的科学资本。但现实更复杂。
课题组发现,大多数科学家没有减少与原籍国家的联系,而是建立起了一个将各国联系起来的学术网络。许多人还回到了祖国。
“大脑流通”似乎更适合描述这类人。研究发现,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或者驻留在哪里,他们的论文引用率,都比非流动科研人员的论文引用率高出40%。
在流动科研人员中,有不到三分之一(占所有流动人员27.3%,即162519人)属于传统的移民科研人员,他们首先在一个国家发表了文章,然后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继续科研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停止了对前一个国家的依附。另外三分之二(72.7%,即433375人)的流动科研人员,在整个科研生涯中始终保持与自己祖国的联系,同时还收获了更多的国际关系。
通过绘制科研人员数量和流量的流通网络,研究发现,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德国是全球科学网络中最集中的节点。对这些国家的隔离政策,将产生巨大后果。
亚洲和北美洲之间流动频繁
接着,研究团队将样本范围缩小,集中在那些于2008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且在2015年之前至少发表8篇文章的人身上。这意味着只专注于研究初级学者,这样避免了与资深科学家的混合,因为后者的流动轨迹和网络会与目标样本有所差别。
在锁定的12046名研究人员中,欧洲占据最大比例,达到了35%,其次是亚洲和北美地区,占到了25%。亚洲和北美之间的关系比较强大,2008年第一次发表论文的亚洲国籍流动科研人员,多数在2015年发表论文时标注了北美洲的地址,而同时北美洲的流动科研人员中也有三分之一在亚洲。这两个趋势可以解释为相同的现象——亚洲学生涌入美国,随后回归亚洲。
数据显示,欧洲科研人员流失22%,亚洲流失20%,而北美地区却收获50%。欧洲科研人员几乎在每一个国家的流动人数中占到了最大比例。
高影响力来自少数流动人员
了解一国对高影响力学者的培育和负责程度也很有意义。课题组通过查看流动科研人员在流动前后的文章引用指数来评估这一点。
北美和北欧国家作为强大的科研人员生产者,他们对人才的投入和培育以及发掘,都关系到其后续的科研影响力。亚洲是人才纳入的强大地区,收获了很多知名科学家。而大洋洲是值得注意的孵化器,能够培育出高潜力的科研人员。
在所有地区,流动科研人员比非流动人员更引人注目,但地区不同,优势各异:高影响力的北欧人被招募到南欧;高影响力的西欧人则被招募到大洋洲和东亚;来自大洋洲的流动科研人员到达北美和南欧时,会获得高影响力的工作;中西亚(包括美国禁止入境的国家)科研人员在北美和欧洲的工作成果获得了最高的引用率。
总而言之,研究团队认为,在流动性、复杂性日益增加的时代,科学劳动力的国际可比流动指标尤为重要,这些指标能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经济的交流提供更细致和更有针对性的评估。
事实证明,国际流动科研人员虽然占少数,但影响力巨大,限制其流动性可能对越来越依赖国际合作的科学体系产生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