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稿与解聘
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我们从这本书洋洋洒洒的行文中可以读出作者在写作时是如何逸兴遄飞、文思泉涌。确实,这本翻译成中文时名为《万历十五年》的书后来被评论为一部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作品,作者试图从中国历史上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解释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何以落后于西方。
黄仁宇四十八岁才入行历史学界,个人作品不多,已近六十花甲的他急需出版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因此这本书是他调动一生的经验和思考,全力以赴的作品,寄出书稿的时候,他充满信心。他认为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在世界史学界引发一场巨大震动。
然而他收获的,却是美国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退稿。市场化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虽然包含宫廷秘史、妃嫔恩怨等普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流行要素,但是又夹杂有大量思辨性的内容,对普通读者来说有很大阅读难度。从本质上来说,这本书应该属于学术著作。
而学术类出版社的编辑看到这本书,更感觉一头雾水,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方式过于文学化,既不像一部断代史,也不像一篇专题论文。曾留学美国的政治学者刘瑜谈起学术界的“规矩”,她说,论文写作“格式化”,排斥个性和风格,不仅国内如此,美国其实也是这样。美国的学术圈子鼓励的同样也是“精致的平庸”,如果你想在这个圈子里生存,就要自觉地顺从“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
美国学术出版的惯例是作品须经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评审。审稿人面对这样“不伦不类”的“四不像”,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提出修改建议。它更像散文或者小说,而不是历史。他们认为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和探讨历史,根本就是错误的。
祸不单行,就在这本书屡遭退稿的过程中,1979年,黄仁宇以六十一岁的“高龄”,被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辞退。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说:
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
“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这是一个突然的打击,黄仁宇完全意想不到,因为到1979年春季为止他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黄仁宇在回忆录中说:“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
相对羞耻,更为难以承受的是经济问题。他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后来回忆说:“我被解聘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
就在被解聘前不久,因为在欧美出版无望,黄仁宇干脆自己动手把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出版的机会。
黄仁宇与黄苗子的夫人郁风的弟弟认识,黄苗子和中华书局的编辑很熟,因此他在1979年5月23日给傅璇琮写了一封信:
璇琮同志: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第一次寄书稿来时,金尧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尽快给他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并说陈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张。但书稿分三次寄来,稿到齐时,尧如同志已离开了。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
匆匆即致
敬礼!
苗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几经讨论和反复,终于在三年后,也就是1982年付梓出版。有意思的是,也许是因为作者的籍籍无名,书的封面上竟然没有出现黄仁宇的名字,只有题字者廖沫沙的名字。
接到样书后,已经六十四岁的黄仁宇心情非常激动。虽然他也指出:“封面上……没有作者黄仁宇的名字,在设计上似欠完善。”但是接下来,他还是在信中一再对中华书局表示感激。他说:“大历史观容作者尽怀纵论今古中外,非常感谢,应向执事诸先生致敬意。”
“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
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包括黄仁宇自己。
为了证实他的激动心情,黄仁宇在这本书刚刚出版时表示,虽然他经济上处于困窘之中,但“不受金钱报酬”。因为“国内作家多年积压书稿亦望付梓,《万》书与之争取优先出版机会,故暂不收稿费及版税”。
后来中华书局向黄仁宇赠送了200册书以充稿费。然而这本书上市后,市场反响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0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在读书界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三联书店拿过这本书的版权,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种出版。虽然没有做任何营销,但是《万历十五年》还是迅速成为大陆最畅销的历史著作,迄今销售已经数百万册,成为现象级出版物。嗅觉敏锐的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台湾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
从此,黄仁宇的作品在海峡两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中国海峡两岸普通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在屡屡碰壁之后,在他被大学解聘后的第二年,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黄仁宇的期待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这本风格独特的书立刻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杂志上为这本书撰写书评,大力推荐,他说:“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1982年和1983年,该书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后来又被以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出版,在美国被一些大学采用为教科书。
如今,这本书已经一纸风行三十年,坊间甚至有“不读《万历十五年》,读遍诗书也妄然”“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戏语。
为什么这样一部最初不被看好的作品,后来在中国大获成功呢?
首先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迅速定于一尊,对历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释,比如五阶段论、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动力论等。历史学界越来越呈现一种僵化、沉闷、压抑的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如此。
《万历十五年》的出现,如同在沉闷的房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刚从“十年浩劫”中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界呼吸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刘志琴在《黄仁宇现象》中说:《万历十五年》在这一时期出版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了民众对教条化的史学读物早已厌倦。且不说别的,就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外屡见不鲜,而在中国30年见所未见;以人物为主线,从政治事端、礼仪规章、风俗习惯描绘社会风貌,就引人入胜;在论理中有故事有情节,具体生动,不落俗套,使读者兴趣盎然。我想,如果不是《万历十五年》而是其他历史著作捷足先登中国,只要有类似的特点,也一样有轰动效应。
其次,这本书的畅销更与黄仁宇独特的叙事策略有关。黄仁宇选择了明朝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平淡的、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的一年,选择了六个人物,用七篇文章来展示大明帝国,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这六个人物是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他们都是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王朝,然而最后,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败下阵来。这六个失败者的群像,组成了一个失败的王朝。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叙事结构就是以一个个人物为中心,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作者把一桩桩历史事件围绕着一个个历史人物,叙述得娓娓动听。
这本书大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通史观。这也几乎是一个规律:大部分影响力很大的通俗史学名著,背后都有一个清晰的观点。毕竟,普通读者选择读历史作品,不是为了学习考证的技术,而是为了获取知识和结论。学者可能乐于展示自己的专业技巧,螺蛳壳里做道场,但读者并没有观察庖丁解牛的耐心。因此,对普通读者来说,好的历史作品是小中见大,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去,能够看到清晰的大的规律。
《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是黄仁宇要展示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全貌。他要告诉读者的是,为什么从明代起,中国落后于世界。黄仁宇的答案是,“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个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大一统体制一方面简单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社会变化发展的空间。传统政治体制的弱点在于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只重道德的表面,而缺乏务实地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如同庞然大物,实际上不堪一击。因此黄仁宇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引入西方的“数目字上的管理”,“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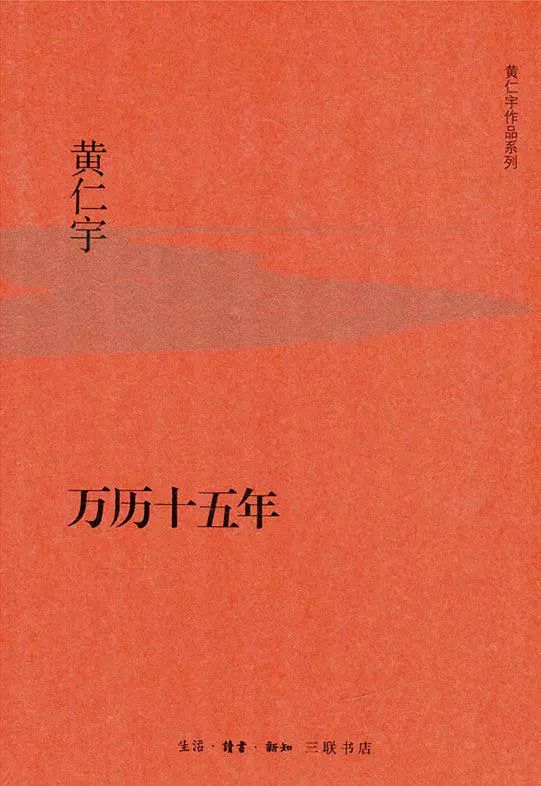
历史界的琼瑶?
为什么黄仁宇能独辟蹊径,写出这样符合读者口味的作品呢?这与黄仁宇的个人特质有关。
黄仁宇的人生是颇有点传奇色彩的。黄仁宇是湖南人,少年早慧,十四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八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不出意外的话,他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机电工程领域大展所长。然而上学不久,抗战爆发,一腔热血的他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曾先后担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后来更是远赴缅甸,1944年5月,因在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
战后他负笈美国,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录取,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读新闻,后转到历史,1954年获学士学位,1957年获硕士学位,1964年获博士学位。

这样的经历,在当代历史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黄仁宇的学术训练可能不够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却也使他没有被学术界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所驯化,保持了强烈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半路出家”使黄仁宇终生保持了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
“半路出家”的黄仁宇的所有思考与写作,都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个人生命中的困惑。“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他说: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 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
黄仁宇个人的独特经历,造就了黄仁宇作品的独特性格,也造成了黄仁宇作品的意外“走红”,更让身处失业阴影中的黄仁宇的生活柳暗花明。如果不是大量的通俗性学术作品在海峡两岸赢得了源源不断的稿费,六十二岁失去“饭碗”的他可能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而通俗历史写作的成功,支撑了他在被辞退后能维持二十年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且在死后让他的妻儿生活有所依靠。
听起来,这似乎又是一个学术界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结尾应该是从此黄仁宇就迎来学术的春天,赢得无数鲜花和掌声。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普通读者可能只知道黄仁宇的盛名和其书的畅销,却不知道他在学术界受到的排斥。学术界对黄仁宇的反应是复杂而意味深长的。“他那标注了‘大历史观’称号的小中见大的史学技巧在让相当一部分人欣喜的同时也遭遇了另外一小部分人的狙击。”
朱学勤对黄仁宇的独特之处表示欣赏。朱学勤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
然而,两岸历史学术界的大部分主流学者,对黄仁宇表示肯定的并不多。有人对他的学术根底表示怀疑。胡文辉在一篇专门批评黄仁宇的文章《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中说: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
有人对他的写作方式完全不认同。黄仁宇在文字表达上的强烈个性和不拘一格,他的混合散文、小说和论文风格的叙述方式,让他的作品在普通读者读来味道浓烈,软硬适度。然而,他也因此备受学术界中那些特别看重学术规范的人的批评。他的文笔在他们看来是“粗野”的,欠缺精准。他的表达方式在他们看来过于注重感觉而非理性。“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
尤其为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很为自己的大历史观自豪,他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他的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迎合了那些想迅速了解中国历史全貌的读者的阅读心理。
但是在学术界看来,他的大历史观“粗糙、粗略、粗浅、粗鄙”,“严重不成熟”。正如耿立群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因此,正统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黄仁宇的见解“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大陆学者认为黄仁宇是“历史学的余秋雨”,而台湾学者则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甚至说:“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除了对黄仁宇的学术思想不认可之外,中国明史学界对黄仁宇的反感,还在于他个人的性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中国明史专家王春瑜在黄氏去世后写了一篇文章,名为《琐忆黄仁宇》。文中说,1988年,明史学界召开国际明史研讨会,因为一位认识黄仁宇的前辈专家的推荐,他们邀请了黄仁宇。结果,大陆学者惊讶地发现这个美籍学者严重缺乏一个历史学家的“风度”:在另一次讨论会上,黄仁宇发言时,说着说着,竟跳起来,蹲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他大概是忘了,这是在国际明史研讨会上,而不是在当年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会上,或训斥国民党大兵的场所。他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与会者的反感。
明史学界反感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明史会议上不规规矩矩谈明史,却谈“大历史观”:更让人不快的是,他在发言中,不谈明史,却大谈所谓“五百年大循环”的“大历史观”,令我辈听之无味。……我说:“这是在中国开会,最好只谈学术,谈明史,免得遭人非议。不能像在美国,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见他的作风与国内学界如何格格不入。
“黄仁宇现象”的反思
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导致了黄仁宇的毁与誉。黄仁宇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有些地方存在很严重的硬伤。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即使以学术圈内的严格标准去衡量,黄仁宇也是颇有一点学术分量的。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都是被认可的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学界泰斗费正清和李约瑟都对他很欣赏,特别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明代名人传》这些重头学术著作的撰写。这都是响当当的学术履历。如果他没有写这么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对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不会受到学术界如此强烈的批评。
黄仁宇评论现代学术的研究方式说:“一般风格,注重分析,不注重综合。各大学执教的,都是专家,因为他们分工详尽,所以培养了无数青年学者,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倒很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形式,非常尊重。”
确实是这样。历史学术研究方式越来越专业化,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趋势。随着历史学越来越专业化,历史学的“致用”价值被“科学化”所遮蔽。许纪霖说:“如今我们的……知识体制所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不再是像陈寅恪、吕思勉那样知识渊博的通人,而仅仅是匠气十足的专家。
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历史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不少治史者犹如‘雨人’一般,除了自己那个狭而又窄的专业领域之外,在知识的其他领域(包括史学的非专业领域),显现出的是惊人的无知。”
大陆学界在这个方面与台湾、与世界大部分地方情况一样。这种情况下,史学和公众的关系也越来越远,枯燥无味到不少历史学者都不爱读。面对社会兴起的“历史热”,历史学界不但罕有参与,而且多抱冷嘲热讽之态度。
因此,黄仁宇虽然收获了普通读者的无数鲜花和掌声,在学术界却是孤家寡人。“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个人创作方面却显得很不幸运。无论是史学界和汉学界,他都没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进行交流的同志,他应该是处在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他在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教着一门并不重要的课程;他所进行的一些学术尝试,也经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响应。”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