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著名当代科学哲学家,美国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迈克尔·斯特雷文斯(Michael Strevens)的新著《知识机器:非理性如何造就近现代科学》中译本出版。这是一本阐述科学为什么在人类社会来得如此晚、又为何如此具有改变的力量的思想性作品。
本书回顾了科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对哲学家的思想及研究进行了总结,对两千年间多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刻画,也用生动的笔触和形象的比喻带领读者走到许多个科学争辩的历史现场,引领读者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的科学与思考的探索之旅。
作者认为,“知识机器”就是近现代科学,它是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机器,能够不断创新并且具有实证性。作者总结提出了统治科学的“铁律”,同时向我们揭示,科学家绝非毫无偏见或者私心的完人,但在科学铁律的约束下,他们自发地把那些偏狭与私欲排除在了科学实证研究的范围之外,在科学争论中,一切都按照游戏规则来。这正是《知识机器》中作者所揭示的,是解释的铁律造就了近现代科学、令这一知识机器以如此大的能量持续改造人类社会及文明的原因所在。而如今,面对全球气候问题、肆虐的流行病,我们人类尤其需要来自知识机器的建议。对此,作者的建议是:“我们重视和赞扬知识机器,给予它成长所需的自主权。”
走出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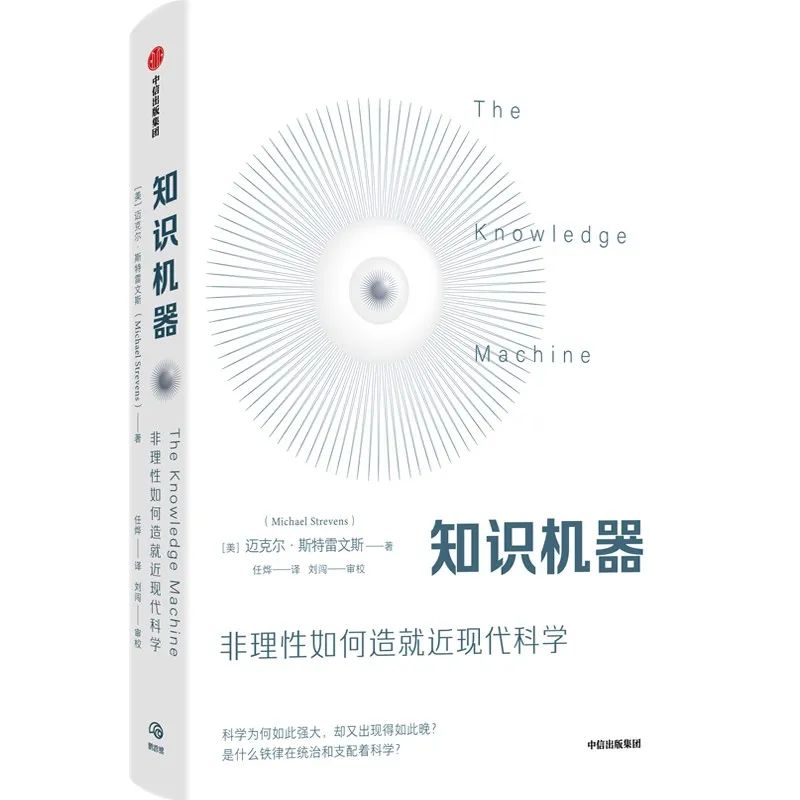
依我之见,迈克尔·斯特雷文斯是当代最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的新作《知识机器》是继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之后最重要的科哲成就。它批判地继承了波普尔与库恩的学说,汲取了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家对传统科学观各方面的批判成果,以高度概括和鸟瞰的眼光,总结出了科学从西方文明中产生并发展的规律和本质,让人们又重新看到了科学的一个总体的、融贯的全方位形象。
迈克尔是著名哲人贝里·勒韦尔(Berry Loewer)的高足,我是10 年前通过贝里结识他的。迈克尔曾多次来访中国,和国内科学哲学界有许多接触与合作。就在最近, 他还应我的邀请,在线上为国内的哲学爱好者做了两场关于《知识机器》的讲座。迈克尔著作等身,在科学哲学的多个领域均有重要贡献。比如,随机过程基础方面,有他的《比混沌更大》(Bigger Than Chaos,2003),科学解释方面有《深度》(Depth,2008),概率的因果基础方面有《第谷术》(Tychomency,2013)。

迈克尔·斯特雷文斯
要想理解《知识机器》这本书并从中获益,首先要知道书中所说的“科学”一词不能从广义上去理解。按广义的“科学” 算,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有科学,中国历史上应该说也有科学的雏形。但这本书中所说的“科学”是当今世界上大部分人赖以生存的那个科学,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不停地运转着 的科学,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各种商品背后的科学。明白了这 一点,那么《知识机器》的主要结论就是: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诞生于17世纪欧洲,是一只非理性的怪兽。依仗独有的“铁律”(iron rule)和对“浅层解释”(shallow explanation)追求,它走出了西方文明,得以繁衍发展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该角 落的初始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去有多么遥远。而书中所谓的“非理性”或“反理性”(irrational),是指科学反叛欧洲博大精深的哲 学文化和基督教传统的实质,同时也指该知识机器在与欧洲传统 哲学和基督教完全相悖的文明/ 文化土壤里生根开花、与之并存的现实。所谓理性,就是与本文明/ 文化的融会贯通。
因此,书中所说的科学之非理性或反理性,并非指科学方法或实践在逻辑意义上有不连贯、不自洽的地方,而是说,科学方法和实践违背了文化传统常识的理性,背离了美或崇高的追求, 在铁律的紧箍咒下,一味追求可通过经验检验的浅层解释。当然,认为科学方法与实践是内在连贯、自洽、统一的整体,展现出高贵、纯理性形象的观点,在库恩以及之后的批判文献中早已经不复存在了。《知识机器》的另一高明之处,也正是在于它吸收了诸多对科学的批判,认清了科学的高效多产并不是因为它具有某种高度统一的所谓“科学方法”,也不是因为其理论能为人们提供对大自然的统一深刻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真可谓一只非理性的怪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人类企图超越自身的文明实体。而缔造这部机器是靠了17世纪文艺复兴后期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自然哲学家们的革命性创举,找到了铁律作为高效出产客观知识的法则,浅层解释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这才为人类真正“寻找到了”科学。
标新立异的结论往往不难想到,要想论证其为真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我认为,斯特雷文斯的《知识机器》一书从理论和历史两个角度,成功地建构了这个论证。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英国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促成了欧洲的自然哲学从以统一和谐的自然观为纲领的自然哲学,通过培根、玻意耳和牛顿等人的贡献,转化成了以取得经验验证的局域性因果解释(即浅层解释) 为纲领的“知识机器”,成功地打造出一套近乎“新型政体”的科学共同体规范。在科学研究的私下领域里,私欲、美感、自然观等偏好,仍然可以任意泛滥;而一旦进入科学知识的公共殿堂,所有的论述都必须接受铁律的严酷裁决。优美的宇宙体系可能会被铁律推翻;再精湛的理论模型与论证,只要没有被实验证实过,就拿不到诺贝尔奖。西方千年哲学和宗教文明编织而成的奇妙宇宙模型,在铁律面前一败涂地。知识机器一旦出生便六亲不认,笛卡儿的宇宙体系输给了牛顿的体系,尽管后者从形而上学来看漏洞百出,连其最核心的万有引力都不知是何物。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派输给了以玻意耳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派,更是标志着科学作为知识机器,摆脱了欧洲文化的限制。和古希腊时期的西方文明一样,世界上其他文明在轴心时代皆有过自己独特的自然哲学,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与古希腊几乎同时。之后中华大地也孕育了多位自然哲学的大家,但是,如果斯特雷文斯的结论为真,科学的出现不是强大的文化、自然哲学传统的产物, 科学反而是摒弃了那种传统才得以出现的。
斯特雷文斯对科学的这一新颖理论,除了为现代科技为何如此晚近才出现于欧洲提供了答案,还解释了科技的传播力为什么如此之强。出自欧洲的其他“产品”,没有哪一样在传播之广、扎根之深方面可以与科学相比。基督教的传播也相当广泛,但很明显,它与科技在今日世界各处的地位仍无法匹敌。科学(和技术)在各种传统文化迥异的地区扎根,靠的不正是在背弃欧洲传统文化时获得的中立性、无菌性和普适性吗?明白了这一点便能看到,当人们用到“西方科学技术”等词语时,他们实际上是误解了这个从西方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模因”a。它出自欧洲(西方),但又是反叛西方的;它由那些已经超越了西方传统文明的科学家延续并传播。每到一处,当地同样能够超越本土传统文化或自然哲学的人很容易地就能学到并继续发展科学技术,以至于到了今天,科学是世界上传播得最广,而变形最少的文化现象。欧洲文明/ 文化出产的其他模因,落到别的地方都多有变异,只有科学不会如此:不会有美国的科学、中国的科学和赤道几内亚的科学之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欧洲科学之所以遍布全球,主要原因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政策吗?怎么可能是由于其内在秉性呢?但是这个理由不成立。如果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主要原因,那么基督教应该和科学一样,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且拥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也可以消除非欧洲文明/ 文化民族在发展创新科学技术方面的自卑。有人称,中国科学家不够多产、创新力不足,是因为缺乏欧洲文化(如古希腊哲学)的熏陶,但在《知识机器》的新科学观看来,这种观点是偏颇的。欧洲人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好不容易才在17 世纪借助殖民扩张的民族热情,摆脱了其传统文化的桎梏,打造出一种六亲不认、似乎来自外星 球的知识机器。本来就不在那种文明之中的国家、民族,应该发 挥自身本来便具有的“外界人”身份,对科学做出更有创造性的 独特贡献。同理,如果想将科学与本国、本民族的文明/ 文化传统绑定,那也必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如我上面所说,虽然科学的铁律要求对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进行严格的“杀菌”,以去杂去污,但是这不妨碍科学家在研究的原创探索阶段,以各自的文明/ 文化背景、哲学人文修养作为灵感来源。欧洲中世纪炼丹术和邪教思潮对牛顿构思万有引力的理论的原始贡献、马赫的实证论哲学对爱因斯坦构思相对论的贡献,以及老庄思想对汤川秀树构思核力场的介子理论的贡献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案例。
总结一下,斯特雷文斯这部《知识机器》,依照我的理解, 可以让我们看到以下几点。
一、科学是在17 世纪的欧洲通过反抗宗教与哲学传统脱颖而出的。
二、铁律清理了科学研究,使其成为独立于区域文明/ 文化的高度有效的“知识机器”。
三、非欧洲文明中不曾有过“科学”并不奇怪,而不受欧洲传统文明/ 文化的影响的科学可能反倒会带来比欧洲更多、更大的贡献。
四、要发展科学为社会造福,一个国家或民族只需要做好两件事情:维护铁律以提高知识机器的效率,合理管理知识机器以使其多造福、少制害。
五、发掘和发展本地域文明/ 文化的自然哲学,为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开脑洞”提供资源。
我向每一位关心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起源问题的学者、学生和一般读者强烈推荐《知识机器》。斯特雷文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还有着十分出众的文笔。这本书的文采,读者从第一页起就能感受到。感谢中信出版社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本颇为忠实原文的中文译本,让他们得以享受这部历史故事生动、哲学论证严谨深邃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