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这几个月看了不少经济系学者写的经济史文章。往往很有收获,但也经常有些隔行如隔山之感。其中一篇的核心论点是:政治领袖们会从自己的社会网络中搜罗亲信,得势之后还会提拔这些亲信(晚清曾国藩首次登上TOP5刊!)。另一篇的核心论点是:被极权国家的领导人指名攻击,会负面影响该国国民的预期寿命。两篇的量化分析都颇有力度,但…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第一篇文章我很熟悉哈。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张教授的总结是文章的其中一个机制,但并不是本文主要的发现和贡献。文章主要是想1)把微观的网络关系和宏观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这一点经济学上研究还不太多,2)用这个例子来看战争怎么影响国家能力—这一点文献上尚集中于税收能力,导致有时候发现内战也会增加税收,和已有理论矛盾。另外,熟悉相关历史文献的读者应该知道,太平天国之后,国家能力变弱是不是由于地方精英的兴起是存在争议的。反对方的质疑是1)国家仍然依赖科举制度选拨替换官员,2)国家变弱的原因有很多种,特别是中外战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仔细看看证据是有意义的。
在我的理想中,批评者读了论文,如果对论文中提到的贡献不满,可以有理有据一一批驳。但理想的读者可能本不存在。所以只要是实名的严肃的批评,我都会尽量思考一下。非常感谢关注和讨论我们的文章。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多谢回应。既然摊开了,那我就直接问了:先不谈这些理论层面的framing,仅从事实叙述层面上,贵文的量化结论和传统史学中的共识有何不同?在我印象中,没有任何清史研究者会质疑“曾国藩从湖南本地的亲属/社会网络中征兵,得胜之后又大力扶植亲信,使得湘军旧部成为晚清政治中的的重大势力”这个叙事。
如果贵文的贡献在于推进我们对于晚清国家能力的认知,那么这种贡献的实证基础是什么?是“曾国藩的亲信网络挑战了朝廷的中央控制能力”吗?这个结论确实是有一定争议性的,但贵文的事实叙述和传统史学中的到底相差多远?归根到底,贵文的重心还是在实证上,不是吗?
您在这个帖子里提到的各种理论视角都是我感兴趣的,可能之前也确实没有多少人把曾国藩这一段历史和这些理论视角相结合。这种结合是有益的,这个我很赞同。但我通篇读下来,并不觉得这种结合才是贵文的重心。贵文的重心无疑是那一套量化实证。因此,我的疑惑始终是,这一套实证刷新了我们哪些传统共识?
退一步讲,如果那种结合才是本文的重心,那么我就比较好奇贵文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确实相当厚实——我之前也表达过这个看法)的实证研究?直接拿传统史学共识作为实证基础,然后流出更多的空间去深入讨论这一段历史的理论意义,不是更好吗?何必先量化复刻一遍共识,占掉了文章绝大部分篇幅?
当然,如果贵文的潜在假设是“只有量化证明才是证明”,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确实隔行如隔山,有些事也没法相互理解。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传统史学方法只能证明某种现象存在,但无法去计量该现象的幅度”。如果这是贵文的基本姿态,那么恕我直言,贵文所用的史料本身颇为残缺且具有selection bias,因此得出的幅度计量并不比之前各种湘军研究更可靠(当然也没有更不可靠)。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张教授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挺好。我不确定什么样的回答格式更合理。暂时把粗略的回答放在这里。我和合作者很愿意和张教授进行一次对谈,讨论这个研究的局限。
1)对国家能力的实证基础是什么?我们看了两组证据,主要是权力如何偏离了依赖科举制度的分配,发现前面微观的机制可以解释宏观偏离的一半左右,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当然很希望历史学家能关心这个发现,但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第二个是东南互保时各地的反应。
2)如果和政治经济学里的理论讨论结合是重点,是不是不需要提供微观证据,引用已有的历史讨论就好了。这是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需要使用经济学的语言与同行对话。
3)有些问题有了历史叙事,是不是需要数据证明?数据证明是不是比历史叙事更可信?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很愿意讨论哈。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多谢贾教授的进一步回应。我的回应如下:
第一,湘军大员的提拔扰乱了正常的晋升渠道这一结论,依然是史学界早有公论之事。姑且不论这几十年来关于晚清督抚政治的各种系统研究(可以用连篇累牍来形容),连当时的政治精英们(如赵尔巽)都在《清史稿》里有过评论。此外,要说起来对于晚清科举晋升的扰乱,军功渠道绝非最重要的,捐纳卖官才是。这一点可见Lawrence Zhang等人的一系列近期研究。
第二,历史叙事也分各种各类。有的比较新,实证根基尚不稳,自然值得量化验证,有些更是有直接争议的,但关于湘军的这些叙事恐怕是在史学界里最没有争议、最根深蒂固、考据最厚重的那一类里。对于这样的叙事,我们的态度是否应该不一样?
第三,我所谓的“占篇幅”不是说贵文不需要量化实证,而是说可以把量化实证的焦点放在一些更有争议的问题上(比如对于国家能力的进一步细化计量)。经济学的量化历史文章我也算是经常读了(不得不读),“把一个在史学界里没有争议的基本共识当作进一步量化分析的起点”这种做法,貌似很常见,也不会影响其他经济学学者对文章的接纳程度。贵文并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到底还是因为不肯相信史学界关于湘军派系的研究吗?为什么?
总之,感谢作者们愿意和我公开讨论这些事。这很难得。三月份在西北的那个经济史会议上,我们不妨继续?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你的【第一】一方面说这个微观机制经常被讨论,另一方面又说总体上其他的机制更重要。这正是仔细看数据的意义之一啊。而且,我们还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军功,网络影响到了很多没有直接参加战争的人。如果这些你认为都是细节或者不相信,我们也好奇能继续做什么。期待更多的讨论哈。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我当然不会不相信(问题是我之前就很相信)。史学界目前的共识是,督抚这一级别之上,军功的效果比较显著(封疆大吏就那么些,这个很明显),但三四品官员之下,捐纳的效果绝对更显著。至于封疆大吏和中低层官吏这两个群体里,哪一个对于国家能力更重要一些,这个我们没共识,但贵文貌似也没什么说法。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1)关于【封疆大吏和中低层官吏】的问题非常好。虽然我们有一些关于quota的结果(对低层重要),但没有看分布的影响。2)关于我们是不是不需要花很多篇幅证明微观机制,而应该更多的衡量国家能力的评论也有道理。我们在后者应该做更多,但没有办法避开前者:前面的结果是计算出最后的分布不同的基础。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以上就是我和贾教授的一系列讨论的集中整理。这次讨论从她和两位合作者关于湘军派系的量化史学新文章(晚清曾国藩首次登上TOP5刊!)引申而来,颇能体现传统史学和量化史学两种学术范式的异同与互动方式。供诸君参考。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感谢总结。这些讨论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文章的辩护,一目十行略过文章的读者未必理解我们想表达的想法,这也是我们写作面临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很希望通过接受批评能把以后的工作做的好一点点。但究竟自己的文章有什么样的读者?随着学科的进展,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还有谁会看这样的文章?我没有答案。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嗯,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税收整体上涨(依靠厘金、关税)也是清代财政史的基本共识之一。我写第二本书的时候,这一点根本就不用我自己论证,引用别人的研究即可。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我的意思是政治经济学里目前只利用税收来衡量国家能力并不完美,会得出能力增加的结论。所以引入权力结构是有意义的。哪怕读一读文章的introduction就能明白我们的意思?唉,我就此打住了。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政治学里有很多这样的模型(王裕华新书里引用了不少),社会学、法学、史学里也多。经济学或许很少,但这背后的原因挺值得玩味的。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如果你的意思是,贵文的真正重心和贡献全在 sec. 5.3 那一两页纸里… 第一这有点难以服人,第二或许这文章的结构确实有点问题…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1)欢迎你提供相关权力结构的文献哈。2)我和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我们的研究对历史学可能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才强调这方面。文章的很多结果对经济学重视的理解现象背后的机制有意义。比如虽然权力增加了,但权力是通过何种渠道增加的?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我以为你不关心,所以没有强调。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将精英构成引入国家能力讨论的政治学著作,仅我比较熟悉的就有Garfias, APSR(2018), Crone, World Politics(1988), 以及Tilly学派的一系列著作。社会学那边也有Skocpol和Mann这种老经典。清史学者里更是常见(近期如和文凯的著作),毕竟晚清财政收入上升而国家能力下降是主流叙事。经济学或许特殊。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至于国家权力如何离散的机制,这个我当然关心,但传统史学叙事里不乏对机制的深入探讨,和贵文所述依然高度重叠,贵文貌似也没有讨论它们。贵校周锡瑞教授曾经和人合编过一本关于晚清地方精英的论文集,是这套文献里比较重要的一本。中文著作如张晨怡、王继平等多人的专著与论文,皆有论述。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3)再举例来说,权力的作用到底持续了多久?到底是领袖关系的影响还是战争动员的影响?是只有网络内部人受益还是有很强的spillover?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有意义的。我之前的讨论试图想告诉你也许历史学家能从数据中得到一些新的见解。但你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我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之前我和张教授的讨论中,我过度地希望告诉他:瞧,数据能对历史学家的争论有贡献吧,所以我集中讨论了历史学家们关于权力变化和国家能力的争论(可以参见McCord(1993)的一些总结)。结果,他好像更关心的是:你们很多证据我们历史学家都说过,你们凭什么发在经济学【顶刊】上?(没想到历史学家的脑筋也被我们的期刊排名所拘囿着)。这个时候,我只能解释说,经济学重视很多现象背后的发生机制。虽然个人或者少数人影响国家命运有很多例子,但这个的发生过程并没有很好的一步步的证据。我们的文章比较清晰地解释了这些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历史学家可能没有说清楚的事情,包括:哪些关系更重要?权力增加是怎么发生的?是通过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到底持续了多久?是主要有本来网络里的人解释的吗?还是绵延到了后代?
这些重不重要呢?正所谓【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我没有想说服张泰苏的意思,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更多的只是不希望充满着热情做相关研究的年轻人被别人的轻描淡写所打倒。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我貌似从未在这场讨论里提到过qje审稿标准的问题。我不认为这种事和文章作者去说有什么意义,因为本来也不是作者负责的。至于机制问题,如果这个帖子的潜台词是史学研究里没法辨析机制,或者是相关的史学文献里没人深入讨论过机制,那就恕我直接呵呵了。从经济系的人那里听到这种论调的次数也不少了。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见下方图片。我可能误会了你的意思。但我想说的已经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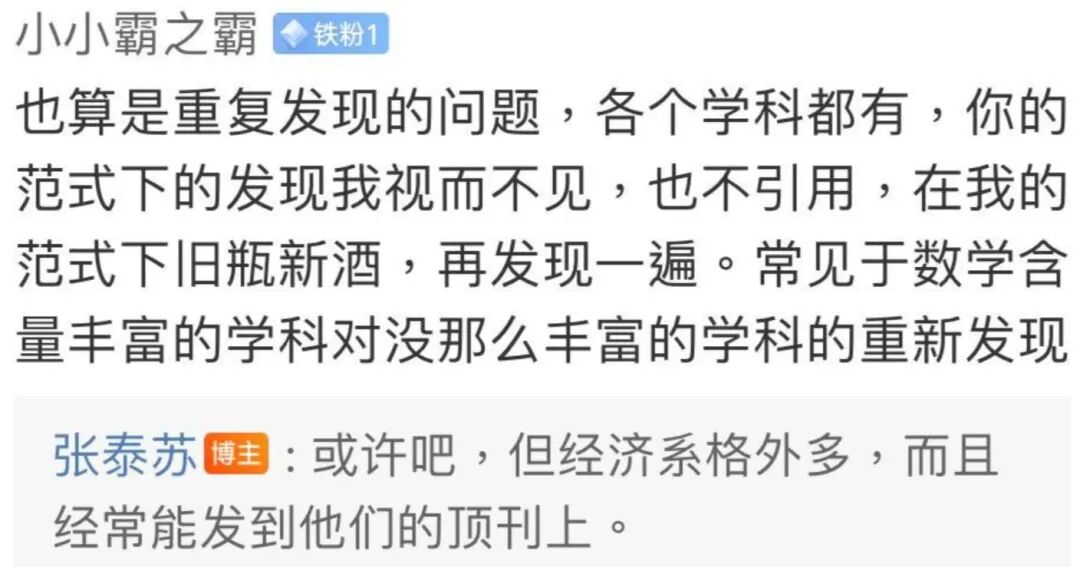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这是个普遍观察,并无贵作不值得发qje的意思。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这么说吧,归根到底,我的观点是:如果是史学界以外的学者研究历史问题(这个无比欢迎),并得出了基本和史学界共识一样的实证结论(这个也很欢迎)时,我希望他们能在文中具体解释一下,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哪些史学界所没能看到的细节和机制,指出了我们的哪些不足之处(这个就更欢迎了),而不是不在文中进行任何讨论,就仿佛史学界数十年的研究不存在,或者做一些诸如“史学研究方法不能分析机制”的无谓假设。这个希望… 应该不过分吧?上述说法里的“史学界”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学术领域,换成“经济学”也无妨(虽然其他领域无视经济学相关著作的可能性似乎要小一些)。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其他学科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推翻史学界的陈年共识,或者在没有共识的问题上制造新共识。这才是跨学科的意义,不是吗?
加州大学(圣迭戈)贾瑞雪副教授:加州大雨,困在屋里适合反思。【史学研究方法不能分析机制】不是我们的假设。我也认同你这些一般性的建议。如果你对我们7-9页上关于三组historical narratives的简介觉得有什么不妥和缺失,我们愿意补充和修正。我也可以总结出来,看能否做的很好。
耶鲁大学张泰苏教授:说到这份上,大家火气也都大了,就先休兵吧。三月份当面聊可能更有建设性一些,起码更容易求同存异。言辞不当之处,我表示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