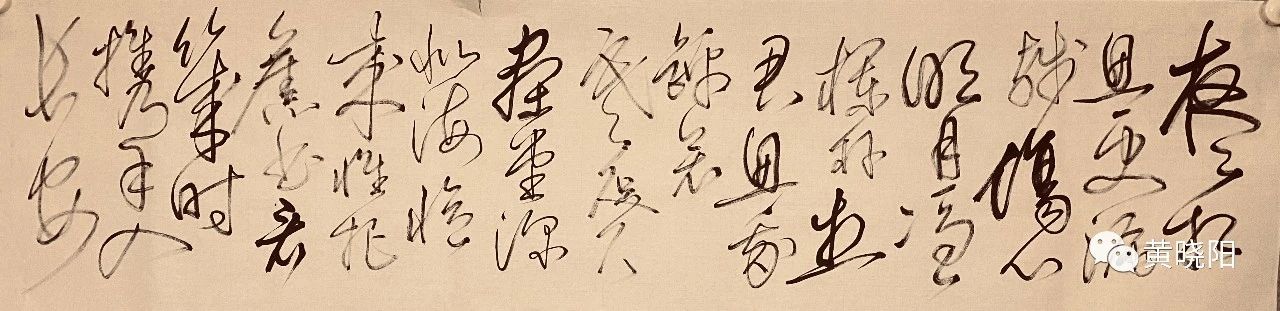
《二号首长》任意一章节,请点击进入:二号首长目录索引
有话在说,请在公众号黄晓阳留言,共性话题我将专文探讨。
姑设一浅譬,如今制,教育部派督学到某几大学去视察,此督学之地位,自不比大学校长。彼之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而止。
但唐代则不然。犹如教育部分派督学在外,停驻下来,而所有该地区之各大学校长,却都是受其指挥,他可以直接指挥各大学之内部行政,而各大学校长俯首听命。
这一制度,无异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之地位。
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
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
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唐代·唐代的政府组织》
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是一种科学,就其结构而言,是典型的形而下,但其设计理论,却是形而上艺术。
既然是艺术,它就应该符合结构学原理,应该有结构美学存在,至少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监察权应该是望远镜显微镜,而不应该是笼子,监察制度才是关押权力的笼子。
监察制度是一个结构,而监察权,既是监察制度的行权工具,也可能是个人的行权工具。监察权一旦被个人滥用,尤其这种滥用成为制度附着物,便如癌变,那就可怕了。
唐代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此。
唐代的监察制度设计并不完善,这也可以理解。
其一,真正形成监察制度,是汉代的事,而汉代的监察制度,又总在左右摇摆,忽重忽轻,忽有忽无。
故此,严格说来,这不是监察制度,甚至只能算是监察认知的对应,是监察作为制度化的发端。
既然如此,不完善不成熟,也就是自然而然。
其二,公权体系中的每一项制度建立的同时,便会受到权私的侵蚀、分化、攻击。
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一场攻防战无休无止。
监察权的滥用,本就是私权作用的结果。
其三,监察权太容易助攻集权,对监察权进行各种限制是势所必然,故此,更容易变动。
钱穆先生说,“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
这恰恰就是监察权越权侵占行政权的结果,而且,这种越权行为,客观的制度设计为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条件之一,皇帝要专权,不敢轻易将权力交到下属手里。
条件之二,中央和地方之间缺了一级行政结构。
条件之三,监察权没有被关进笼子里,也就是不受监察。
如此一来,哪怕监察使官虽然品级很低,基本和县令平级,却有权监察刺史以下所有官员,监察权也就成了高高在上的上位权。恰好填补了中央到州之间,缺了一级行政结构的空白。
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
我不知道钱先生一再赞许汉代的郡县两级地方结构,是否认定两级是最为科学的地方结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汉代的两级郡县结构,让中央管理三百多个郡国,是极不科学的。
别说三百多个,就是一百多个,都根本管不过来。
唐代将全国分为十五道,这是为了执行监察权,一道也要监察约二十个州。且不说范围广权力大,一个监察使,管着二十个州,相当于现在两个省,根本就忙不过来。
早在汉代,地方监察官员由巡官变成一级行政官员,出现了州一级类行政结构,刺史变成州牧,就已经是监察权侵凌行政权的滥殇,原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可毕竟,汉朝之亡,并非亡于监察权的过度滥用,唐朝因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别说唐代,就是到了明朝,监察权的泛滥,达到了极致,才引起后人的重视。
钱穆先生说,“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我想,他的这句中央集权,不应该理解为皇帝集权的中央集权模式,甚至不是御史台对监察权的集专,如果理解成上位权的专控,或许就可以说得通。
另一方面,形成这种局面,源头确实是皇帝想搞中央集权。
皇帝想集权,而自己是孤家寡人,肯定集不了。他必须要用一些人,这些人便成为皇帝集权的工具。之所以能成为工具,恰恰在于皇帝向他们放权。
这种权一旦下放,便会在这些人身上,形成权力堰塞湖。区域权力集中到了这些人,比如唐代的巡按身上,不可能集中到皇帝手里,所以,集权的努力,反倒成了权力的流失。
皇帝后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以后在尚书省也搞了一个巡官制度,称为行省。
行省基本和监察区的道重置,此举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