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斯特拉·桑福德是伦敦金斯顿大学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欧洲哲学教授。她的著作包括《植物的性别:植物哲学》(Vegetal Sex:Philosophy of Plants,2022)《柏拉图与性》(Plato and Sex,2010)和《如何解读波伏娃》(How to Read Beauvoir,2006)等。本文原载于aeon.cn网站,原标题为:“重新认识植物——植物令人惊叹的复杂行为引发了我们思考世界的新方式:植物哲学”(Seeing plants anew — The stunningly complex behaviour of plants has led to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our world:plant phil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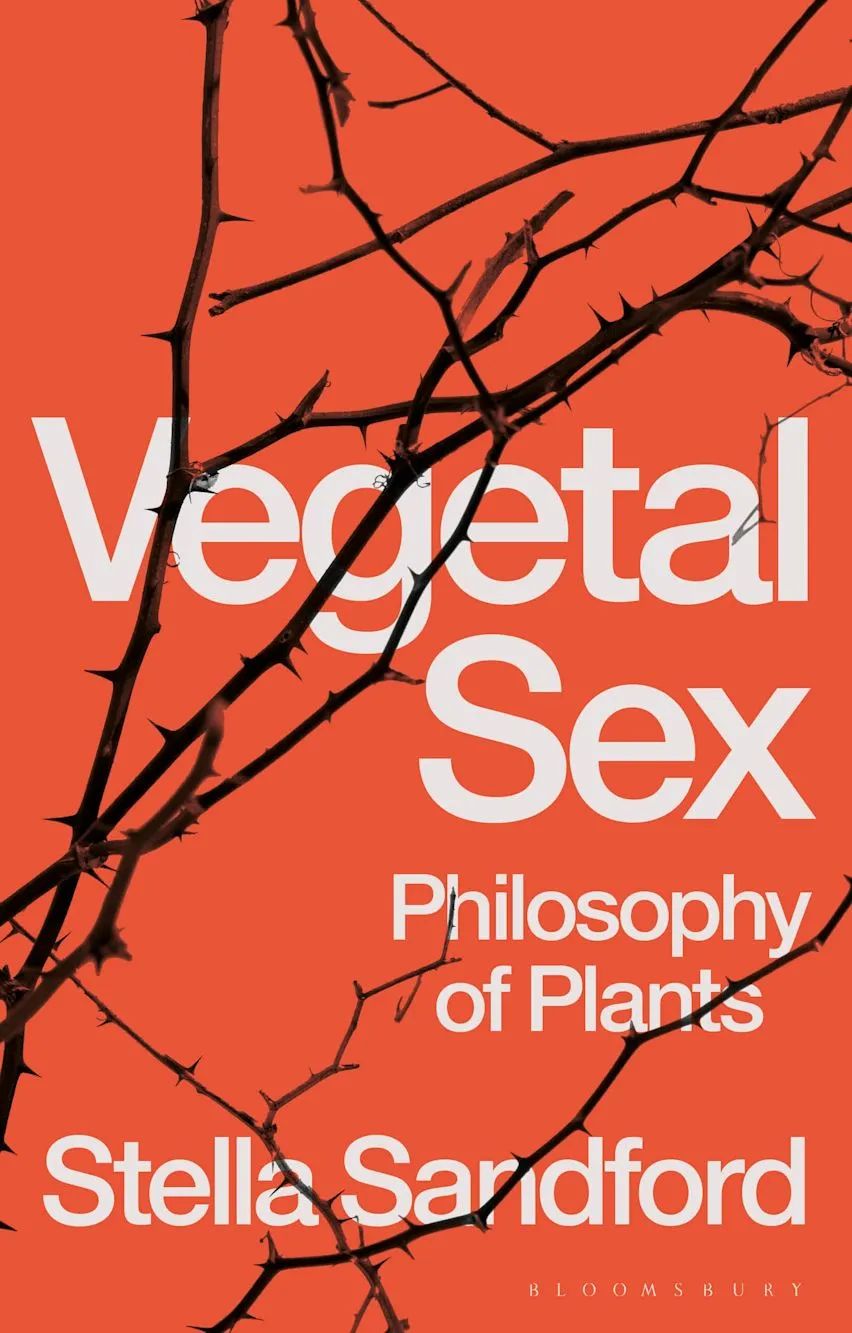
《植物的性别:植物哲学》(Vegetal Sex:Philosophy of Plants,2022)书封
至少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曾经普遍认为,植物于动物生命而言是被动、惰性的背景,或者仅仅充当着动物的饲料。诚然,植物自身可能十分迷人,但它们缺乏动物和人类的许多有趣之处,例如能动性、智慧、认知、意图、意识、决策、自我认同、社会性和利他性。然而,上世纪末以来,植物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彻底推翻了这种观点。我们才刚刚开始窥见植物与环境之间、植物彼此之间、植物与其他生物之间异常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对植物的认识能取得这些重要进展,主要归功于植物行为研究(the study of plant behaviour)这一特定的研究领域。
鉴于“行为”一词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的联系,“植物行为”的概念可能看起来有些奇怪。当人们想到经典的动物行为——蜜蜂跳舞、狗摇尾巴、灵长类动物相互梳理毛发——我们可能会好奇,植物生命中会有哪些与之对应的行为呢?
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哲学家罗素(E. S. Russell)是动物行为研究之重要性的早期倡导者之一。1934年,罗素主张,生物学应从研究整个有机体开始,并将有机体视为一个动态统一体,经历着维存、发展和繁殖的循环。他认为,这些活动都是“目的指向的”,正是这种“指向性”活动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区分开来。按照罗素的说法,行为涉及有机体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是这种“有机体一般指向性活动”的形式。这意味着植物和动物一样,都会表现出行为。但由于植物是固着的(sessile),它们的行为主要表现在生长和分化中(胚胎细胞发育成植物的特定部分),而不是像动物那样表现在运动中。
到20世纪末时,我们对植物行为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生长和分化的范畴,并且这种理解还在继续扩展中。正如植物学家安东尼·特雷瓦弗斯(Anthony Trewavas)所言,植物行为就是“植物所做的事情”。事实证明,植物确实会做很多事情。让我们以受伤为例,大多数植物通过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来应对叶片受到的伤害。其中一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能激活非生物应激相关基因(abiotic stress-related genes),另一些则具有抗细菌和抗真菌特性。有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专门用难闻的气味或毒素驱赶攻击植物的食草动物;有些植物可以识别出是哪种特定的食草动物正在攻击自己,并相应地作出不同的反应;还有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会吸引正在攻击植物的昆虫的天敌。食草动物的攻击还能诱使植物分泌更多的花蜜,从而促使昆虫远离叶片。(注:一种间接防御机制。)
这些反应很容易被理解为“目的指向性”行为——指向植物自我保护与繁衍的目的。它们很可能赋予植物适应性的优势。但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释放也会诱使邻近植物在自身受到攻击之前产生同样的反应,即使它们是不同的物种。一些实验似乎表明,植物有可能对那些它们认为与自己具有亲缘关系的植物(由同一种植物的种子生长而成的植物)表现出不同的有利行为。例如,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凤仙花种植在共用的花盆中,以研究它们如何应对地上光照和地下根系空间的竞争。他们发现,在有亲缘植物的花盆中生长的植物茎干更长、分枝更多,而与非亲缘植物生长在一起的植物则长出了更多的叶子,阻碍了其他植物获得光照。因此,植物似乎与亲缘植物进行合作,而试图与非亲缘植物进行竞争。
植物的“存在”挑战了主导西方传统的一些重要假设
对一些科学家来说,这项研究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它为植物科学开创了新的范式,并且提出了一种新的植物生命观。现在许多人认为,这项实验的结果要求我们承认,植物具有先前被认为是动物甚至是人类所独有的特性和能力。在一些人看来,如果不借助相关术语,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科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
这些重要的进展也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关注。科学哲学是哲学学科中一个成熟的分支领域,而生物学哲学则是科学哲学中的成熟分支。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似乎是新的东西:一个专门思考植物问题的哲学领域——“植物哲学”。它不仅是对植物科学研究的元批判分析,而且还受到植物科学研究的启发,对植物重新展开哲学思考。
新植物哲学的出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植物科学的回应,尤其是对其中新范式的回应。标志了新范式的一系列概念——能动性、意图、意识等等——早已成为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主题。一旦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植物上,更广泛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不仅是因为哲学对植物感兴趣,也因为我们发现,植物生命或植物存在(plant being)的特殊性,挑战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来主导西方传统的一些重要假设。植物哲学不仅关乎植物,还关乎植物生命的特殊性如何迫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来思考自身的存在。
在一些人看来,“植物哲学”这个概念似乎很荒谬,就像某种新潮的时尚,并且你也不会在任何一本最新的哲学词典中找到它的条目。但事实上,植物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几乎与西方哲学史一样悠久。亚里士多德为理论植物学奠定了基础,他将生物定义为自身具有营养、生长发育和衰亡能力的事物。只有某些自然事物具有生命的潜能,而“灵魂”就是这种潜能的实在(reality)。因此,只要生物是活着的,它们就拥有灵魂(希腊语的“psuchē”翻译成拉丁文即“anima”,意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分为三个“部分”:“营养灵魂”“感觉灵魂”和“理知灵魂”。“营养”能力是生命的基本原则,是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物所共有的。此外,动物具有灵魂的“感觉”部分,而人类则独有“理知”的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营养部分的功能是利用营养和生产(即后来所说的繁殖),这两者都是一种“运动”或“变化”。由于植物也拥有这种灵魂,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它也被称为“营养”灵魂或“植物”灵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被认为丧失了感觉或思维能力的受损人类,会被称为处于持续的“植物”状态)。
直到17世纪,亚里士多德关于植物灵魂的思想在植物学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举一例:佛罗伦萨哲学家安德烈亚·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的《植物》一书(De Plantis,1583)第一次对植物进行了科学意义上的分类。他认为,植物的本性在于营养和繁殖的功能,因为这是它们所拥有的唯一一种灵魂的“本质”。随着全球航海时代的到来,大量不同的植物物种被发现,对植物分类系统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植物的分类系统被认为应当基于植物的本性。因此,切萨尔皮诺根据产生种子与果实的方式,建立了他的植物分类系统(在属的层次上)。在致他的赞助人阿方索·托纳布奥尼(Alfonso Tornabuoni)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自己之所能成功地制定这一分类系统,是因为他将“植物学专业知识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没有哲学研究,(植物学)就无法取得进展”。
植物学史将 19 世纪从哲学中获得“解放”视为其科学进步的关键因素
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相关思想的继承也推动了植物学研究。在其生物生育理论中,亚氏认为,雄性“原则”有能力通过为其他被动(雌性的)物质“赋予灵魂”来传递运动或生命。但由于亚氏的生育理论实际上只是关于动物的繁殖理论,这种雄性力量通常被定义为制造感性灵魂的力量。由于植物不具有感性灵魂,因此植物似乎不可能存在雄性和雌性之别。但是,如果像亚氏认为的那样,雄性原则生成了更普遍的生命或运动,那么,既然植物是有生命的,植物中就一定存在雄性与雌性之类的差异。
这一难题困扰着植物学早期历史上所有的开拓者们。但它非但没有阻碍研究,反而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虽然在植物生理学中,没有与动物的性器官和性物质相对应的明显特征,但研究人员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与之相应的东西,因为植物和动物共享了负责繁衍的“植物灵魂”。英国植物学家尼希米·格鲁(Nehemiah Grew)被认为发现了花朵的生殖器官,这一发现正是缘于他在寻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雄性器官”(或功能)的生命原则。格鲁将这一原则与花粉联系起来,尽管这种联系是混乱的。
如今,植物科学认为自己与哲学毫无关系。事实上,植物学史将19世纪植物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视为其科学进步的关键因素。但是,这忽略了一些最重要的植物学研究者的哲学热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科学工作。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脱离关于现实本质的基本形而上学假设,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坚持把植物学与哲学相分离也意味着,我们将无法理解植物学在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让-雅克·卢梭(1712-1778)都热衷于植物学。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这只是一种非哲学的爱好吗?还是他们对植物的研究影响了他们的哲学思考?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们又回到了新植物哲学,它既试图挖掘哲学与植物学相互纠葛的历史,又旨在重新激活两者之间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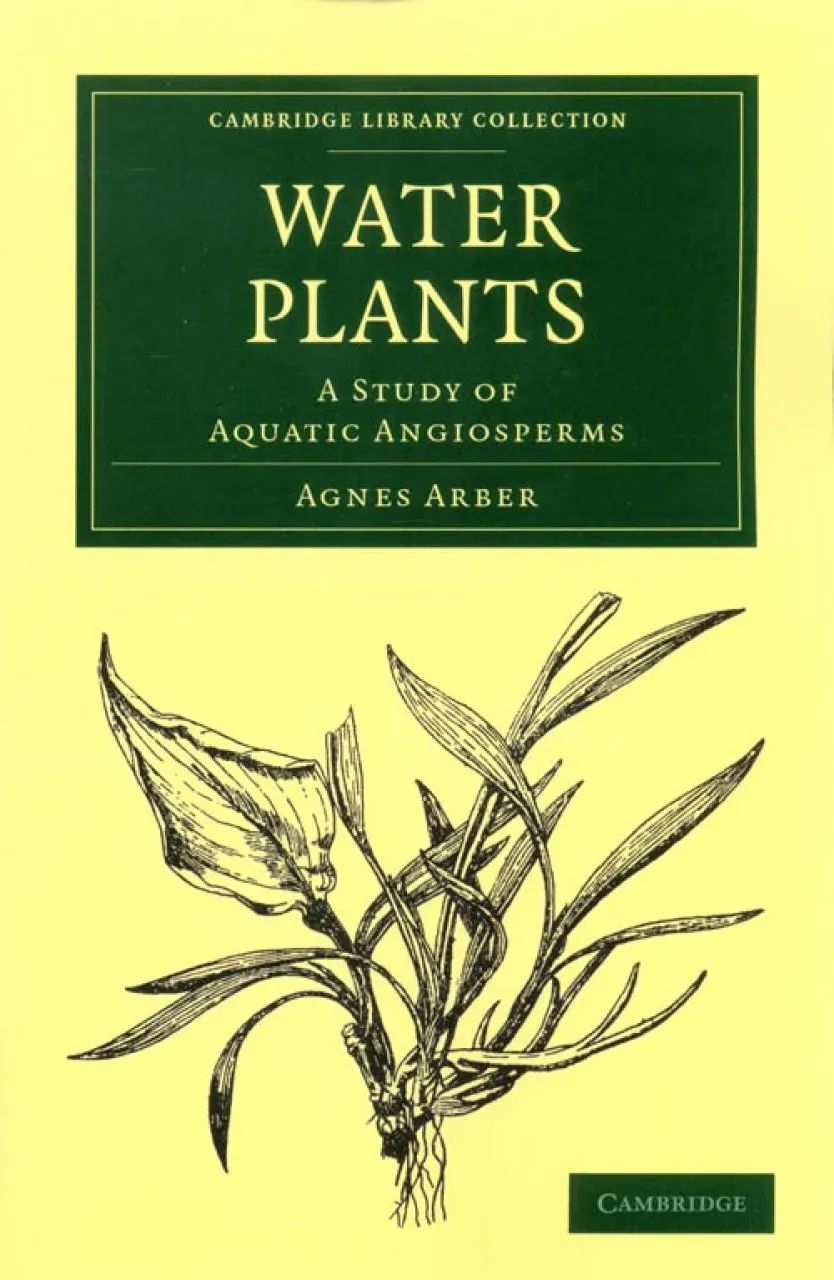 《水生植物》(Water Plants,1920)书封
《水生植物》(Water Plants,1920)书封
英国植物学家阿格尼丝·阿尔伯(Agnes Arber,1879-1960)是20世纪深耕这一领域的杰出人物,她主张将历史和哲学研究视为现代科学实践的一部分。阿尔伯在许多文章和专著中对植物形态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水生植物》(Water Plants,1920)《单子叶植物》(Monocotyledons,1925)和《禾本科植物》(Grasses,1934)。在《植物形态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 of Plant Form,1950)中,她的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得到了明确阐述。对阿尔伯来说,植物形态学——对植物形态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植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而是对植物形态进行的更全面的研究。她回溯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eidos)概念,并将其理解为“任何特定个体都是其内在本质的体现”。她的这种理解大大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将“内在本质”涵盖了植物的整个生命史,包括植物的大小和外形的变化。这将形式重新定义为动态的,并拒绝对形式进行与功能相分离的分析。这一“形式”概念对阿尔伯至关重要,它让她看到了纯粹分析方法所忽略的方面。
阿尔伯论证了植物畸形学对“正常现象”的研究非常重要,对此,斯宾诺莎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阿尔伯将植物的“异常现象”,即“未被实现的潜能的揭示”,表述为“植物能做什么”的说明,这呼应了斯宾诺莎“身体能做什么”的名言。她的枝叶关系理论明确引用了斯宾诺莎关于“自我持存的冲动”的论述。对阿尔伯来说,这些哲学资源是她提出植物学假说的灵感来源。随后,她试图用通常的科学方法,即通过观察获得的证据来证实这些假说(这通常是成功的)。
阿尔伯强调哲学对植物学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最近得到了一些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支持,他们为当代植物哲学的一个分支做出了贡献。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西斯·哈雷(Francis Hallé)专门研究热带雨林和树木结构(他参与发明了浮筏,这让科学家第一次能够进入热带树冠层)。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思考,对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专注于化学时,以及“将植物简化为染色体数目、碱基对序列、拉丁二项式、细胞器的电子图像、曲线上的一点、一份参考书目、计算机存储器中的一个数据、离心机里的残渣或试管底部的愈伤组织(callus)”时,我们失去了什么——哈雷正是其中的一员。除此以外,哈雷在他的书《植物礼赞》(In Praise of Plants,1999/2002)中提倡回归对植物的整体研究,“从它的根到它的花,它的土壤,以及它在历史上的用途。这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感官来感知它,而不仅仅是以一种思维的、失活的方式。”
对植物生命本体论的思考具有超越植物的意义
在哈雷看来,对植物生命的特殊性进行反思,不可避免地会引出哲学问题,而植物学家和哲学家同样需要探讨这些问题。如果动物个体是一个单元(珊瑚是一个例外),而植物是通过单元的重复而发展起来的,那么植物“个体性”的本质是什么?动物和植物的“个体”概念是否相同?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个体性”的概念,以便将植物纳入其范畴?
法国生态学家雅克·塔桑(Jacques Tassin)同样坚信,在理解植物生命的过程中,哲学是不可缺席的。他的著作《植物在想什么?》(À quoi pensent les plantes?,2016)从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出发:成为植物意味着什么?塔桑认为,这一提问很有必要,因为“不可抗拒的动物中心主义让我们根据动物的状态来衡量世界”。诚然,基于动物生命的模型在植物研究中很有帮助,但我们是否也需要根据植物自身的模式,找到更贴近植物自身“存在”的方法来研究植物呢?
很显然,对植物生命本体论的思考有着超越植物的意义。无论是在西方哲学中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倾向于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进行思考。这些占据支配地位的对立项的集合,被认为在思维中捕捉到了类似于现实结构特征的东西,一些人将其简称为“西方形而上学”。它们包括内/外、物质/形式、心灵/身体、个人/集体、生/死、一/多、男/女等对立项。20世纪西方哲学和相关领域(如女性主义理论)的很大一部分都致力于对其中的一些组合进行批判性研究,有时甚至是正式的“解构”,但它们仍然形塑了我们大部分的思想与行动。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因为它们很有效,而且确实描述了我们经验的直观特征。譬如,在冬天,屋子里比屋外暖和,因此我想保持内/外的区别,非常感谢!这些区别可以在日常使用的环境中存在,并能包容一些极限情况(例如,一扇打开的窗户通向一个微风习习的房间)。这当中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当这些区别的有效性与现实各方面结构中的明确划分相混淆时——当它们成为强烈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时——它们可能是阻碍性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尤其因为,这些二元对立通常是根据历史上确立的等级制度来发挥作用的,在其中一个比另一个享有特权或更受重视)。如果自然和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在这些术语中根本无法得到充分的描述(是的,自然/社会是其中的另一种区分),那么它们的假定就会妨碍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因此,植物哲学的另一个分支聚焦于,植物的存在在多大程度上无法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术语来充分描述。譬如,如果把植物生命的某些方面划分到个体/集体的任何一方中来理解的话,它可能无法捕捉到植物模块化结构或重复现象的迷人之处。这表明,这种形而上学区分的普遍性假定是错误的。在著作《植物思维:植物生命的哲学》(Plant-Thinking:A Philosophy of Vegetal Life,2013)一书中,哲学家迈克尔·马尔德(Michael Marder)甚至认为,植物的存在“引爆”了西方形而上学:“植物的存在本身就完成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生动的破坏。”
如果说植物存在的基本特征无法通过西方哲学传统的对立概念来充分理解,那么这一哲学传统的某个意想不到的特征就浮现出来了。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哲学是在最高抽象层次和纯粹的“智力”领域中运作的,但它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可能只是从具体的动物生命中被剪裁出来的。关于人类存在的哲学思考,需要从承认人类有限的、具身的社会心理存在开始。但是,一种包含了植物存在的形而上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新的范式,在对植物行为的解释中,我们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一些通常与哲学而非科学相关的术语,如“意向性”“行动”与“目的”。植物智能的概念是其中的核心。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智能”是动物行为的独有特征,认为它依赖于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或者它是一种具有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有机体的可量化的属性或能力,那么我们当然会拒绝植物智能的概念。不过,植物智能的支持者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否认这种假设的合理性。
我们完全可以提供适用于植物行为的“智能”定义,并且我们已经将这个词应用于非生物。如果把生物个体的智能定义为“个体一生中适应性变化的行为”,并将其区别于由基因决定的发展过程,那么将植物行为描述为智能即是有意义的,并且进一步明确植物的定义也是可行的。因此,特雷瓦弗斯将植物智能定义为“个体生命周期内的适应性变化行为”。植物中这种适应性变化行为的例子包括:根部朝向水源定向生长、向光性(植物朝向光的方向生长)、释放挥发性化学物质作为对食草动物攻击的反应。
这里所使用的“智能”的一般定义意味着,任何不具有智能的生物(不能使自己的行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生物)根本无法生存。因此,根据这一定义,智能是生物体能够生存的内在特征。它并非是对人们可能在某些植物行为中认识到的特定特征的定义,否则缺乏这一特征的其他植物行为则可被归类为非智能的。相反,它把智能作为研究一般植物行为的不证自明的起点。这里的任何争论都不是关于某种行为是否是智能的分歧——在后者中,双方都会尝试收集实验性证据以证明该行为是否符合智能的标准。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智能本身的定义。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是智能?植物科学的新范式背后不可避免地蕴含着这个哲学维度。哲学是这种植物科学的一部分。
我们真的需要“能动性”这个概念来理解植物的表型可塑性吗?
当然,我们不必等到植物科学中出现这一新范式——如果它确实是一种新范式的话——才提出“生物智能”的概念。在这方面,植物智能并不像它乍看之下那样不可思议。它只是将现有的关于生物智能的思想扩展到了植物。何乐而不为呢?但新范式并不止步于此。例如,有人声称,植物智能要求我们也将植物视为“能动者”,或者被赋予了能动力量的生物,而不是一种按照程序对外界条件做出机械和化学反应的活体自动机。正如特雷瓦弗斯和西蒙·吉尔罗伊(Simon Gilroy)在2022年写道的:“有许多行为都证明植物是能动者,它们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可塑性。”
那么,什么是能动者?拥有能动性意味着什么?植物是否与动物,尤其是人类一样具有能动性?吉尔罗伊和特雷瓦弗斯将植物描述为“自主地引导自身行为,以实现外部和内部的目标或规范,同时与现实世界的环境进行持续的长期互动”的能动者。例如,在一项实验室实验中,生长在干燥土壤和充足光照条件下的植物长出了较大的根系(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土壤水分),以及窄小、节水、角质层厚的叶片;而生长在潮湿土壤和相对阴暗条件下的基因复制体则长出了宽大、角质层薄的叶片(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光合作用面积)。因此,我们说植物是能动者,因为 “它们会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型(phenotype),以提高生存能力”,这种调整被称为“自主行动”。但是,我们真的需要“能动性”这一概念来理解和欣赏植物的表型可塑性吗?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植物,我们究竟能获得什么呢?
生物学哲学家萨米尔·奥卡沙(Samir Okasha)在他所说的“有机体作为能动者”的论断和“有机体作为能动者”的启发性方法(heuristic)之间进行了有益的区分。前者对有机体是什么样的存在提出了本体论的主张,奥卡沙将它与生物学中反对以基因为中心的范式联系起来。而“有机体作为能动者”的启发法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出于科学理解的目的,它将有机体视为具有目标的能动者。
不过在实践中,这种区别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进化生态学家索尼娅·苏丹(Sonia E. Sultan)在她的植物研究工作中提倡所谓的“生物能动者视角”的“解释策略”。这种策略使得科学家能够解决基因中心主义方法在解释上的一些缺陷。这听起来更像是“有机体作为能动者”启发法,因为它强调的是植物能动者假设的解释性收益,而不是在本体论上对植物有机体给予关注。但是,苏丹也写道,能动性是生物系统的“一种经验属性”,“是有机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组成系统对环境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能力”。能动性视角“始于对生物是能动者的观察”。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生物是如何发展、运作和进化的。
但是,能动性视角到底增加了什么?它是否抓住了新范式提倡者们想要表达的植物能动性与植物智能的理念?它是否捕捉到了植物存在的特殊之处呢?
苏丹认为,能动性概念或许可以为发育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中有关基因表达、发育、遗传性质和适应基础的新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能动性”本质上是这样一个术语,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基因转移到主动反应机制上,这种机制会导致在某些情况下可遗传的发育变化。因此,“能动性视角”并不一定是对植物特殊能力的归因,而是可以理解为对以基因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进行补充的研究方案。此外,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哲学家一样,苏丹明确否认能动性视角意味着植物具有任何行动的“意图”,更不用说是有意识的意图了。
植物研究新范式的倡导者们不仅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案,而且试图用一套来自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概念以构建一幅植物生命的新图景。我称之为“植物鼓吹文学”(plant advocacy literature)。因为除了其科学基础之外,它也代表了植物,并为植物发声。其目的不仅是推动植物科学的发展,更是为了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植物,珍视植物生命并给予它们更多的尊重。
许多这类文献都并不回避使用“意图”的语言,而是畅谈植物的“选择”。譬如,特雷瓦弗斯声称,研究表明,沙丘上的克隆植物(clonal plants)生长在资源丰富的区域而避开资源贫乏的区域,这就让人“难以避免地得出结论:植物存在意图与智能选择,并具有选择有益栖居地的能力。……对栖居地的有意选择是显而易见的。”在其著作《植物行为与智能》(Plant Behaviour and Intelligence,2014)中,特雷瓦弗斯将“目的”或“目标”的含义等同于“意图”,并作出了以下结论:植物确实有意抵抗食草动物,也确实有意对重力做出反应,但这仅仅意味着“植物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并采取行动应对那些削弱了自身生存和/或繁殖能力,从而削弱了其适应性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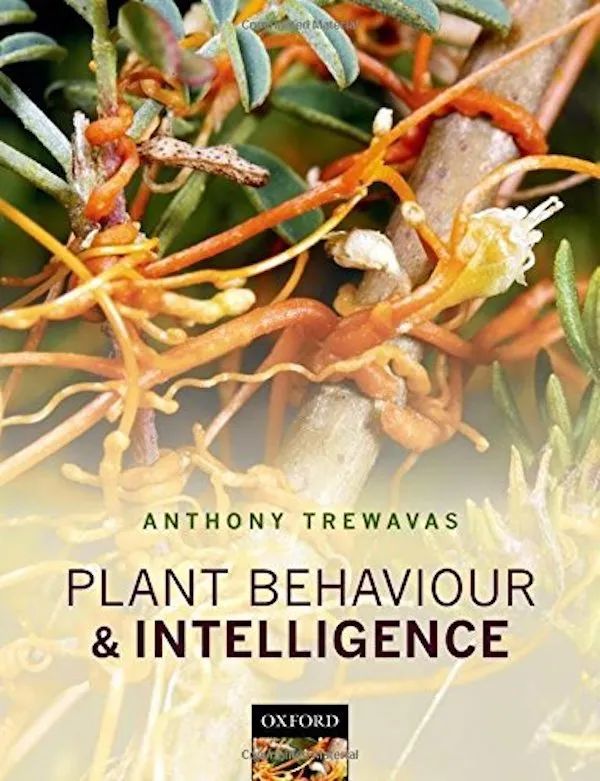 《植物行为与智能》(Plant Behaviour and Intelligence,2014)书封
《植物行为与智能》(Plant Behaviour and Intelligence,2014)书封
然而,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图”和“选择”叙述,在有关植物的流行著作中大行其道。意大利植物学家斯特凡诺·曼库索(Stefano Mancuso)和亚历山德拉·维奥拉(Alessandra Viola)甚至声称,植物自己选择了固着的生活方式,选择了由可分割的部分组成。流行读物的读者们看到的是,植物通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进行的交流被称为植物之间的对话,通过菌根从老树向幼树进行的营养传递则被形容为母亲对幼树的哺育。这种将植物拟人化的做法与植物哲学的目标背道而驰,后者的追求是(尽可能)将植物理解为植物——从植物的术语,而非动物或人类的术语来理解植物。
在日常生活中,欣赏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另一种生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植物哲学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它不仅要努力澄清在植物科学中使用能动性和智能等概念的合法性,而且要找到概念化“植物行为”的方法——这种方法既要避免基因决定论的预设,又要避免某些植物鼓吹文学和大众媒体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或动物中心主义。当然,这种重新概念化的行动将包含现有的生物学哲学思想,但也必须超越它们。
生物学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都是一般性的生物学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原则上涉及所有的生物体以及它们共有的生命过程(例如进化)。而植物哲学专门关注植物,研究植物区别于大多数动物的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对一些一般性哲学问题的影响。我们是否必须重新认识“个体”的概念,才能把由重复单元构成的植物视为一种个体?如果我们开始尝试用“植物行为”来构建一种关于生物能动性的一般哲学解释,而不是事后再将其纳入其中的话,这会产生一种新的“生物能动性”概念吗?在日常生活中,欣赏这些生活在我们中间的别种生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正是它们让我们得以存活。
当代植物哲学才刚刚开始提出这些问题。对此,答案依然是开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