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卡在这里无效”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总统开启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形象和风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然不是人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美国了。这不禁让我回想起曾经访问美国的那些往事。

2004年7月,我进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工作。工作后不久,我便有幸获得了去美国访问的机会。这是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的国际访问者项目,为期大约一个月。我参与的是其中的东北亚安全项目,一同参与的还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学者、官员以及记者。美国国务院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颇具知名度,许多中国学者都曾从中受益。
参与这个项目,让我深切体会到了美国的自信与开放。在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走访了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参加了美国国防大学的学术会议,还参观了位于华盛顿州的美国波音公司、美国第一军(First Corps)军部刘易斯堡(Fort Lewis)、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北美防空司令部,以及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

北美防空司令部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修建的,旨在应对可能爆发的与苏联的核战争。其核心设施便是我们参观的夏延山核战碉堡,它深藏于夏延山山腹之中。一进入碉堡,便能看到两道厚约1到2米的钢铁大门,据说这是为了抵御核冲击波和核辐射。我们乘坐一辆电动车,行驶了好几千米,才抵达山腹内部。接待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北美的防空地图,并解释了在“9·11”事件发生时,北美防空司令部为何应对困难。原来,当时北美的防空雷达是沿着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陆地外缘部署的,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以及美国国内,并没有防空雷达。这就意味着,在国内,美国当时无法实时追踪飞机的动向,只能依靠飞机自身的应答识别系统。然而,美国正常情况下有几千架飞机同时在空中飞行,相关人员很难识别出哪架飞机偏离了航线。令我深感意外的是,美国军方竟然如此“信任”我,让我深入到美国核心军事基地内部参观。当我出来时,还看到许多美国民众在排队等待进入。
在美国第一军军部开会时,接待人员突然告知我们,美国第一军司令就在旁边的会议室开会。这又一次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美国在机密处理方面看似很“随意”,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机构开放的背后,有着一套完善的保密制度作为支撑。有一次,朋友带我去他工作的单位——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参观。这里在冷战时期是美国生产核材料的重要场所,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哥伦比亚河和亚基马河交界的沙漠地带,其前身是在“曼哈顿工程”中生产美国原子弹核材料的汉福德基地(Hanford Site)。参观期间,我去了一趟洗手间,朋友就站在门口能看到我脑袋的地方等着我。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应该是保密条例的规定,外来人员不能离开东道主的视线。美国人就是这样,努力在保护国家机密、增加透明度以及保护个人隐私之间寻求平衡。
除了上述机构,后来我还多次去过白宫、国会、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商务部以及国防大学等位于首都的重要机构,还有位于科罗拉多的美国空军学院。美国成为我访问重要国家机构数量最多的国家。
美国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美国人的多元与包容。
有一次在科罗拉多的美国空军学院参观时,正好赶上中国的春节。美国接待方安排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中国学员为我做引导。午饭期间,值日军官对着能容纳千人的餐厅宣布,今天是全球中国人的春节,让我们一起祝现场所有的中国人新年快乐。顿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我心里满是喜悦。
2016年夏天,我到夏威夷参加了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PCSS)为期一个月的反恐怖研修班。一些学员来自阿富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其中很多人对美国的反恐怖政策颇为不满。在一次活动中,中心主任,好像是一位退役的中将,询问大家: 你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是哪个?有一位来自中东的学员站起来直言:“是美国。”花着美国的钱,这位中东老兄可是一点都不避讳美国人的感受。而这位主任听后,却笑眯眯地说,我就知道会有人这么看。看样子,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反对意见而生气。
我的第二次在美国长时间的访学活动,是由华盛顿大学组织、美国能源部支持的不扩散出口控制研修项目。这次访问持续了半年,我先后在加州位于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的蒙太雷国际问题研究院(MIIS)不扩散研究中心(CNS)、乔治亚大学(UGA)国际贸易与安全研究中心(CITS)和华盛顿大学(UW)国际关系学院访学。
这一次,美国人的体能与健康状况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刚到西雅图不久,我的朋友兼东道主马克(Mark Leek)带我在周末去一个岛上郊游,主要活动是去他的一位亲戚家做客,顺便帮忙砍树。那对老人住在树林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房子就会被周围的树林遮挡,难以照到阳光。我和马克轮流上树,拉锯挥斧。说起来有些惭愧,我虽然出身农家,但自从进城学习工作后,就变得四体不勤。我比马克年轻很多,可体力却远不如他。马克当时已经50多岁了,每个周末还会绕着华盛顿湖划上一圈。在西雅图居住的3个月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美国人的动手能力和身体素质。有一次,我和马克正在院子里砍木材,准备周末的烧烤。该项目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协调人琼斯(Christopher Jones)教授来了,他笑着对我说: 你肯定想不到,你到西雅图来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砍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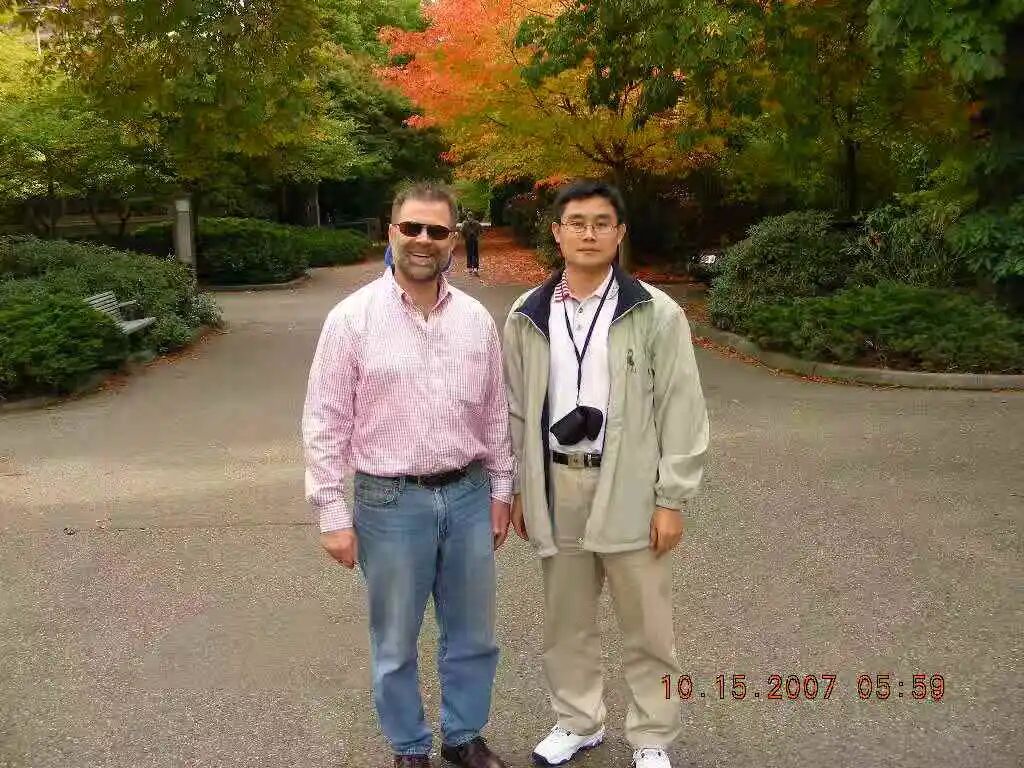
后来,一位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前辈告诉我,在美国交朋友,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美国人是否愿意和你聊体育,是否邀请你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回想当年,我那时并没有领会东道主的良苦用心。
美国人的包容与慷慨,至今仍让我历历在目。
西雅图是我在美国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差不多有3个月。在那里,我住在东道主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全球安全中心主任卡罗尔(Carol Kessler)家里。卡罗尔免费为我提供住房,只需要我在她出差时帮忙照料她家的一只猫和一只狗,偶尔带这两个小家伙出去遛弯。说实话,与猫狗如此亲密相处,对我来说还真是个不小的挑战。我曾问马克,卡罗尔为什么不收我的房租?马克说,就是想让我感受到美国人的善意与慷慨。后来马克多次来上海,每次我都会请他吃一顿大餐。
在华盛顿时,东道主经常邀请我参加各种宴会活动,从在自家院子里的烧烤到周末去饭馆犒劳自己。参加的人形形色色,有消防员、小学老师、智库学者。有一对夫妇,曾是美国和平队的成员,他们曾在尼泊尔参与修路工作,经常跟我讲述在尼泊尔工作时的点点滴滴。在美国生活时,在一些小城市、小乡村的活动中,我还经常遇到前大使、有国外工作经历的前将军。美国的国际化程度深入到了各个角落。看来,美国维持霸权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由美国的角角落落共同承担的。

当时,我在复旦大学的月工资只有4000元左右。去美国之前,我刚买了房子,背负了一大笔贷款,还欠着同事和朋友的钱,女儿一岁左右,正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房贷的“快乐”时期。在西雅图时,由于美方财务方面的问题,我迟迟没有拿到津贴,带去的钱也快花光了,心里充满了焦虑。东道主担心我想家,周末总是邀请我参加各种晚餐。虽然参加这些宴会能品尝到美食,但其实我在吃饭时常常感到心虚。一顿晚餐,开上两瓶红酒,每人再点些餐点,人均消费在50美元左右。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好在东道主很快察觉到了我的窘迫,每次买单时,总会笑着推开我的卡。琼斯教授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卡在这里无效。(Your card does not work here.)”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那笑眯眯的面容,也时常浮现在我眼前。
这些都已经是15年前,甚至近20年前的事了。回想起当时美国人的开放、大度与慷慨,再看看如今个别美国人的自私自利与封闭保守,我不禁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当年的那个美国,究竟去了哪里?到底是美国变了,是我变了,还是大家都变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