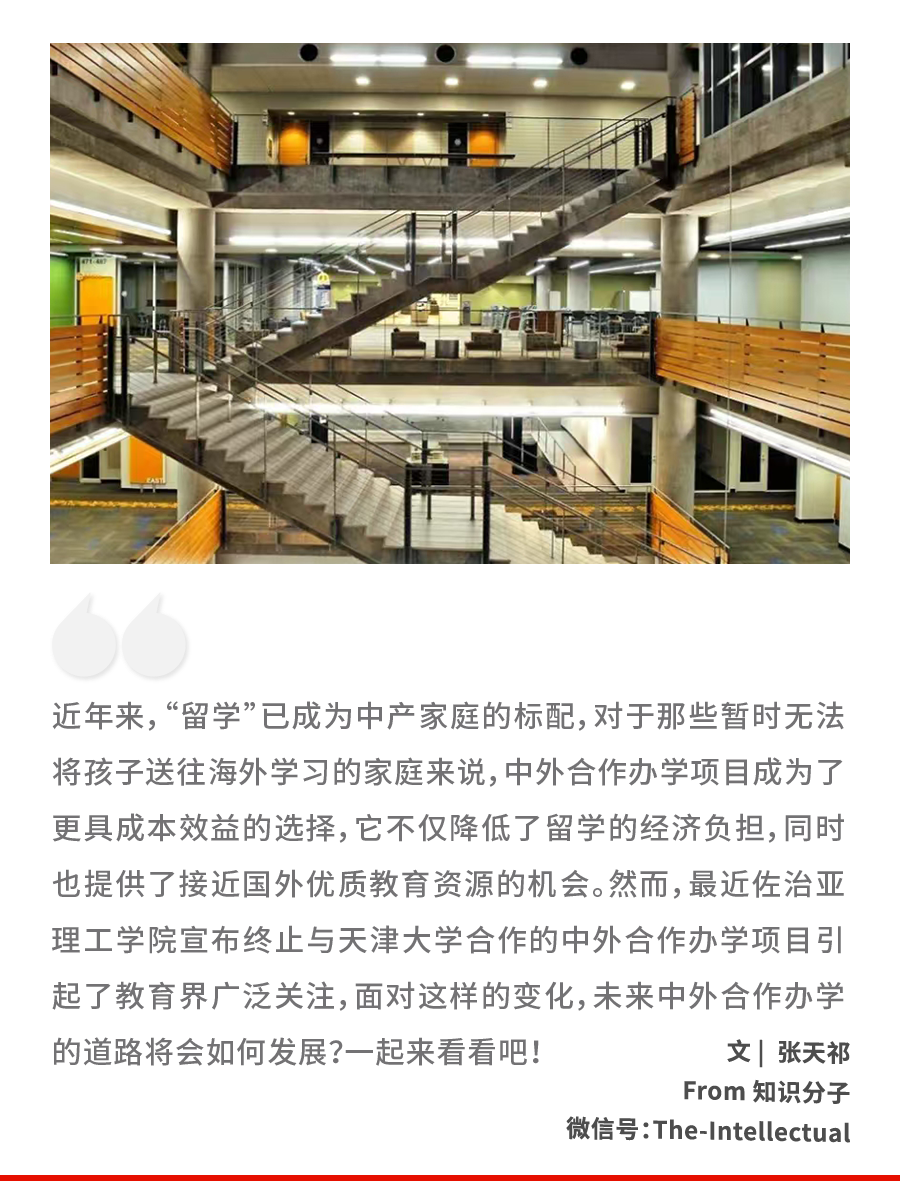
2024年9月6日,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宣布终止参与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GTSI)。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是佐治亚理工大学与天津大学合作的项目,2016年12月,佐治亚理工学院与天津大学和深圳市政府达成协议,在深圳正式开始学院的建设。
从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上可以查询到,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已经审批通过,属于教育部予以资格认定的中外合作办学单位,项目有效期到2036年12月31日[1]。
202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将天津大学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该清单列出了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外国组织。作为一所接受大量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高校,安全问题对佐治亚理工学院来说更为敏感。为了应对审查,佐治亚理工学院决定不启动计划中的博士项目,并将学生人数限制在原计划的 10%。但佐治亚理工没有立刻退出,还在继续观望[2]。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佐治亚理工学院发言人阿比盖尔·塔姆佩(Abbigail Tumpey)表示,自天津大学被列入实体名单以来,佐治亚理工学院就对项目展开了自查,而且一直在评估自己在中国的立场。但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也无法避免政治上的责难[3]。
今年5月份,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新任主席开始把矛头指向佐治亚理工学院,致函佐治亚理工学院校长,要求校方详细说明与天津大学的所有合作。
天津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合作的研究进展,成为了政客集中攻击的对象。今年1月,佐治亚理工学院学者德希尔(Walter de Heer)和与天津大学纳米颗粒与纳米系统国际研究中心合作,研发出全世界首创的功能性“石墨烯半导体”。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声称,该技术可能应用于量子计算能力,他们还引用了媒体说法,声称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中国突破美国对先进半导体的卡脖子[4]。
校方解释,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的工作专注于教学而非研究。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没有从事任何研究工作,没有促进技术方面的转让,也没有向中国提供联邦资金。佐治亚理工学院教务长兼学术事务执行副校长业表示, 国会的质疑“全部没有依据”。
然而,鉴于国会正在考虑新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将禁止与实体清单上的公司有合作关系的美国机构获得联邦资金,学校决定终止合作关系。“对我们来说,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5]。

佐治亚理工事件只是一个开始。9月23日,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责中美合作的研究在推动了中国实现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第四代核武器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等军民两用、关键和新兴技术的进步。
在这份报告中,清华-伯克利深圳研究院(TBSI)、佐治亚理工学院深圳研究院(GTSI)和四川大学-匹兹堡研究院(SCUPI)等中美合作教育机构被点名批评。
报告认为这些合作项目成为了将关键的美国技术和专业知识转移到中国的重要渠道。参与合作办学的美国学者前往中国进行研究合作,为中国学者提供建议,教授和培训中国研究生,并与中国公司在其专业领域进行合作,这都成了怀疑知识转移的理由[6]。
这与已经终止的中国行动计划遥相呼应。同样是怀疑和指责接受美国资助的学者向中国转移知识和技术,只不过中国行动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在美的华裔学者,这次则是针对在华的中美合作机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佐治亚理工学院都对报告提出了异议,伯克利校方还在声明中表示,原则上伯克利开展的研究是向全世界开放的,该校未发现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伯方教职员工有从事其他目的的研究。
但考虑到地缘政治的敏感和委员会的施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告知委员会,该校 "已开始放弃对 TBSI 的所有所有权",并 "正处于解除该联合法律实体的初期阶段"。此前,佐治亚理工学院已经退出了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项目。
与此同时,包含中国众多高校的实体清单仍在拓展,2024年5月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公告修订美国出口管理条例(EAR),在实体清单中新增37个实体,中国科技大学赫然在列。
中科大遭到限制也和“安全”有关。BIS给出的理由是,中科大获取并试图获取美国原产的物品,以支持中国量子技术能力的提升[7]。
中国方面,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引进速度也放缓了脚步。教育部今年更新的中外合作办学名单中,仅有6个新项目得到了批准。与2023年启动的59个合作办学项目和2022年启动的66个合作办学项目相比,这个数字要少得多。
这一方面是源自对质量的要求。2022年,中国本科以上的合作办学项目已经达到了1300余个,数量上并不稀缺。2018、2019年,教育部还依法批准286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止办学。从统计上看,中国双一流高校的中外合作项目集中于STEM专业和经管类专业。在STEM跨国合作日益敏感的今天,这些相对高质量的项目可能在合作上受阻[8]。
另一方面,政治气候的冷暖变化同样影响中外合作项目和院校的生存,这不仅限于中美之间。中澳关系曾经一度降到冰点,2019年前,澳大利亚已经在华设立了100多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但此后合作办学项目少有通过,即使是2022年后两国关系有所缓解后也是如此。
在众多中外合作项目中,有12所中外合办高校拥有独立法人地位,今年通过审批的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是其中最新的成员。
与其他合作项目、学院或中心相比,有独立法人单位的合办院校具有相对较高的自主权。它们在自主选择和自主任命的管理层领导下运作,有权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拥有国家统一招生方式之外,进行独立招生的特权。部分合办院校授予国内学位的同时还要授予国外学位,这要经过国外相关协会的认证,因此学术和管理上会受到中方更少的干预。
不过,这种自主权也是因院校而异的。据《高等教育内情》(Inside Higher Ed)报道,尽管外国合作方往往坚称自己保持了对学术的完整控制,但可能没有资源和意愿保持管理上的平等,而是由中方主导管理。这更像是麦当劳那样的特许经营,外国的材料和技术加上中国的制作[9]。
纽约大学和杜克大学这样的名牌顶尖大学不会放弃对其教育项目或海外业务的控制权,因为这样做的公关弊端太大。但很多非名牌大学的模式会更接近特许经营。
一些教职员工认为,这种管理模式下学术自由受到了挑战。在某中外合作院校的一位讲师表示,美国教师习惯于在机构的管理中拥有发言权,但在中国管理者是家长制的,学校的管理结构里没有教师的位置。另一位讲师则提到,他因为课堂上的发言被中方管理人员训斥[10]。
2018至2019年度,来华的美国留学生数量仍然超过一万,但在2020到2021年度下降到382人,疫情结束后仍没有太大恢复。教师也是如此,“一些在合办学校工作的外国教学研究人员,在疫情过后出于种种考虑迟迟不返回中国,有些直接离职了。”一位研究人员向《知识分子》介绍。
曾任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在2021年曾经讨论过中外合作院校面对的难题。随着中美紧张局势的加剧,有人怀疑美方会关闭校园,也有人怀疑中方会关闭校园,没有人能说清楚。校园的运营一直夹在中美之间,处在不确定性的迷雾中[11]。
去年11月,杜克大学校长文森特·普赖斯(Vincent Price)表示,杜克大学领导层在考虑是否在 2027 年与当地合作院校续签合同时“必须保持清醒”。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建设和运营中外合作院校成了一个难题。
“如今,世界似乎在合谋让这类项目变得非常困难。”

















